|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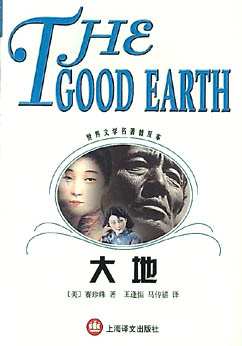 赛珍珠1973年在美国去世,距今整整40年了,但是,考察和研究赛珍珠在中国的译介,主持“赛珍珠专题研究”栏目,特别是近期走访赛珍珠生活过的安徽宿州,参与她的“中国故乡”镇江今年9月举办的赛珍珠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论坛,我感觉她的影响一直都在,而且与日俱增,她仿佛还和我们在一起。这想必都是因为她的精神、她的跨文化理想,以及她一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付诸实施的行动吧。 赛珍珠1973年在美国去世,距今整整40年了,但是,考察和研究赛珍珠在中国的译介,主持“赛珍珠专题研究”栏目,特别是近期走访赛珍珠生活过的安徽宿州,参与她的“中国故乡”镇江今年9月举办的赛珍珠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论坛,我感觉她的影响一直都在,而且与日俱增,她仿佛还和我们在一起。这想必都是因为她的精神、她的跨文化理想,以及她一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付诸实施的行动吧。
赛珍珠虽然从小就爱看中国小说,也酷爱狄更斯描写英国社会底层的作品,但她并没有刻意要当小说家,更何况在中国,她渐渐知道,小说不过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已,因此没多高的地位,事实上地位很低,写小说在人们眼里好像是一件堕落的事,所以,赛珍珠小时候也只是喜欢看小说,在镇江和中国小伙伴跑到打谷场上看戏、听书,直到1917年婚后在安徽宿县(今宿州)几年,家长里短,田间地头,和中国农民特别是农妇聊得多了,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观察多了,思考多了,有了大量积累,这才于20年代末年,写下久熟于心的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故事,即代表作《大地》。
《大地》 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要知道,在赛珍珠拿起笔来写中国农民之前,她看到的类似作品中,中国人“总是拖发辫(不用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佝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了窃盗、强奸、暗杀、毒谋等等看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举动”。而在《大地》中,中国人这一负面形象被彻底扭转。你在这里看不到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人,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长年累月,抗争着天灾人祸,虽然身上有些固有的弱点和陋习,却更散发出人类普通成员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小说1931年一问世,就在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让他们看到中国农民兄弟身上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力。可以说,《大地》通过对中国形象更加实际的塑造,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切、更有感染力的描写,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赛珍珠厌恶把中国人写成古怪和粗野之人的作品,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力把中国和中国人如实地写进她的小说。今天,考察她创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中国人的作品,我们有理由说,她做到了。她写中国农民,写中国城镇的名门望族,写中国知识分子,写中国革命者,写中国留学生“海龟”,当然,在她的作品里,她特别关注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而在构建这些人物画廊的过程中,赛珍珠为了帮助欧美人克服对异质文化所怀有的傲慢与偏见,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补课,使得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以及民风习俗(如包办婚姻等)。在文学创作中有机地穿插文化背景知识,赛珍珠是希望美国人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关注和理解历史悠久、充满情感和智慧的中国文化元素。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赛珍珠因为种种机缘,长期研读中国古典小说,后来还花了几年时间,在中国文人龙墨芗的协助下,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名,翻译了70回本的《水浒传》。她写中国题材小说,译中国小说,更是在阅读和翻译中国小说的过程中,开始研究中国小说;而在研究中,又多以西方小说特别是英国小说为参照,得出了不同于时人的观点,并在美国重要报刊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小说的文章,其中以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中国小说》为顶峰。她面对西方观众侃侃而谈,大力宣传中国小说,追溯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她甚至说她想不出西方文学里有任何作品堪与 《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相媲美。她还特别强调,中国小说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长发展的,我们岂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评估它们的价值?赛珍珠这是在倡导对待不同文化时应遵循的平等原则;在她看来,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才是一条坦途。
1938年后,赛珍珠开始利用自己新科诺奖得主的身份,积极参与和组织社会活动,让世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她长期在中国生活,后来又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对中美相互之间抱有的文化偏见和敌视态度非常清楚,甚至是感同身受,所以,她有一种强烈的对话意识,一旦有机会,就禁不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她作为社会活动家所参与和组织的跨文化活动中,包括了许多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如1941年她创办的东西方交流协会。
在协助《亚洲》杂志编务期间,赛珍珠意识到,单凭一本杂志恐怕教育不了美国民众,想要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能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讲话的中国人,让他们直接面对美国人,举办讲座,讲解亚洲和中国知识。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达成理解。于是,赛珍珠找到访美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如演员王莹),来实施她这个交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