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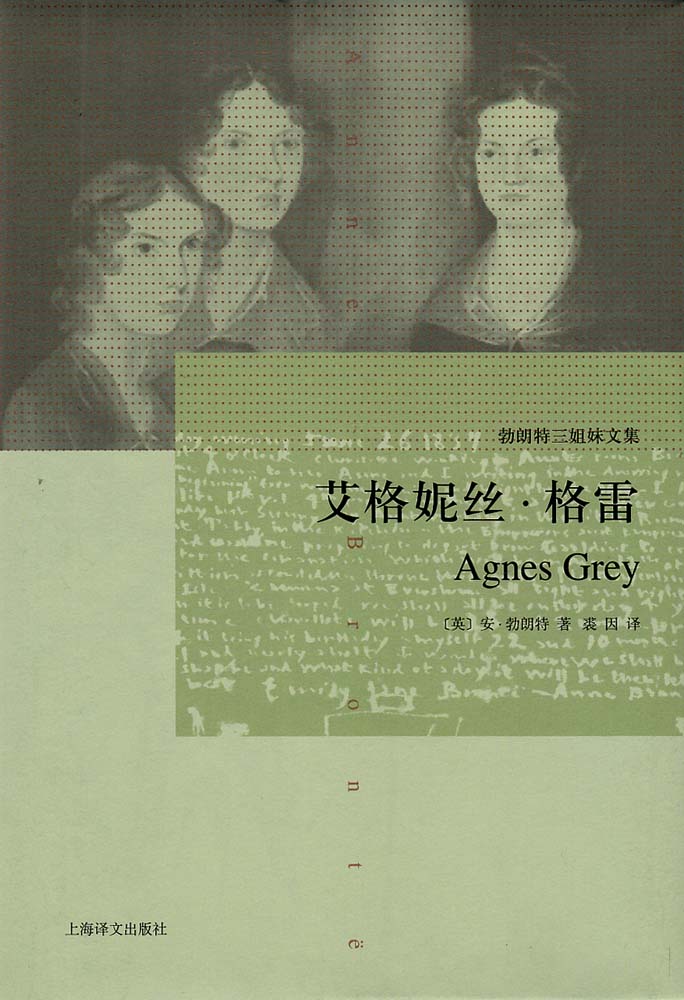 对于勃朗特家几个孩子在母亲生命垂危日子里的举止,盖斯凯尔夫人曾有过一段堪称文学著作中最值得人们回味的描述: 对于勃朗特家几个孩子在母亲生命垂危日子里的举止,盖斯凯尔夫人曾有过一段堪称文学著作中最值得人们回味的描述:
……这六个小孩子常常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朝着阳光明媚但又荒无人烟的原野走去,一路上年长的孩子细心地照料着蹒跚学步的弟弟妹妹;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十分热爱这片荒野。
盖斯凯尔夫人还说,他们“比起同龄的孩子更为严肃、安静,也许是因为家中有着垂危的病人而感到压抑的缘故吧”。一位仆人说得更加坦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孩子。我老觉得他们精神压抑,同我见过的其他任何孩子都不一样。”
勃朗特太太1812年结婚,1813年到1820年间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安妮最小。安妮出生二十个月后,母亲就因胃癌去世,当时才三十九岁。自安妮满周岁之后,勃朗特太太就卧病不起。一位知情人曾告诉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太太“不大愿意多看见自己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明知孩子们很快就要失去母亲,看到他们会使她十分难过”。
这时,勃朗特太太的姐姐伊莉莎白·勃兰威尔从家乡康沃尔来到这里为他们料理家务。威尼弗雷德·热兰是这样描写这个家庭的:
哈沃斯的牧师住宅是一幢乔治式的庄重大方而结构匀称的房屋,修建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但它只有五间卧室,其中一间就在门厅上面。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没有壁炉;另一间是在后间上面,比杂物间稍为大些。勃朗特夫妇、六个孩子、勃兰威尔小姐、两个仆人和勃朗特太太的护士就挤在这五间卧室内。四个大女孩睡在卫生条件最差的一间里。晚上,她们睡在小行军床上,白天把行军床折叠起来,这个房间就变成了育儿室。就是在这间房里,那几个活下来的孩子一直住到十几岁。他们在那里玩耍、写作,享受着绝对的自由。这个房间长九英尺,宽五英尺七点五英寸。
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出色地叙述了勃兰威尔小姐对哈沃斯的感情以及孩子们对她的感情:
勃兰威尔小姐……有强烈的偏见,很快就对约克郡抱有厌恶的情绪……她怀念农村小镇上小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愉快的社交活动;她怀念自幼熟识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成为她朋友之前曾经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不喜欢约克郡的许多风俗,特别害怕哈沃斯牧师住宅的过道和客厅中石板地的阴冷和潮湿……孩子们很尊重她,对她抱有一种因尊敬而产生的好感。但是我认为,他们从没有真挚地爱过她。在勃兰威尔小姐这样的年纪.像这样完全改变环境和住处,确实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她并不想留在哈沃斯充当几个外甥女的母亲的角色,但是勃朗特先生费了很多周折仍无法找到一位新妻子,她也只好留了下来。
虽然勃兰威尔小姐很喜欢安妮,但她对安妮的态度,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阅世不深的老处女突然有机会将她塑造儿童的理论付诸实施时的样子。从安妮来说,她的性格就是喜爱并依恋大人,这无疑也激发了她姨妈的感情。不过,勃兰威尔小姐用来培养孩子的似乎是卫理公会的那套严厉的恐吓办法。威尼弗雷德·热兰认为,“勃兰威尔小姐完全以冷漠而武断的神气来阐述关于爱的宗教的信条,似乎这首先是一种有关恐惧的宗教。”她向安妮灌输一种罪恶感,这使得她一生都处于同这种意识斗争之中。
玛丽亚是勃朗特家的长女,就是夏洛蒂在《简·爱》中曾亲切地提到的海伦·彭斯。玛丽亚对待弟妹更像一个母亲。这是伊莉莎白·勃兰威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首先,玛丽亚的智力同她弟妹相仿,而他们的姨妈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玛丽亚七岁就会“拿上一张报纸关在房间里阅读,等她走出来时就能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大家”。勃兰威尔小姐的文学情趣寄托在《妇女杂志》这类消遣性文学和耸人听闻的《卫理公会杂志》上,仅限于旨在迎合维多利亚时代处于更年期的未婚姨妈、未婚姑妈的病态情感的种种梦想和幻象。
安妮年纪最小,又常常因患哮喘而躺在床上,因而受姨妈的影响最为直接。这种影响本来是会无法估量地增长的,但是在勃朗特太太过世三年以后,家里就把玛丽亚、伊莉莎白和夏洛蒂送到柯文桥为牧师女儿开办的学校(《简·爱》中的劳渥德)学习。这时安妮和艾米莉就给留在家里听任自流了。她们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但是三个月后,家人又为艾米莉打点行装,将她也送到柯文桥学校去了。在艾米莉离去时,家里又解雇了两个年轻女佣南希·加尔和萨拉·加尔姐妹。自从勃朗特一家来到哈沃斯以来,加尔姐妹一直是孩子们的保姆。八个月以后,玛丽亚和伊莉莎白相继去世,剩下的几个姐妹又在家里团聚了。
由此可见,安妮的童年充满着令人心酸的经历——死亡、离别、疾病,又没有母亲般的人时刻支持着她。她从未有过安宁的生活。就像勃朗特太太在病中不愿意见到孩子时的感情一样,帕特里克·勃朗特决定不同孩子们共进正餐。盖斯凯尔夫人机智地解释说,她“不得不”单独用餐,“是为了获得消化食物所必需的安静环境”。勃兰威尔小姐也尽量在自己房间里用托盘吃饭。因此孩子们就只能自己玩耍和相互做伴了。他们的整个世界就是牧师住宅和荒野。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社会交往,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