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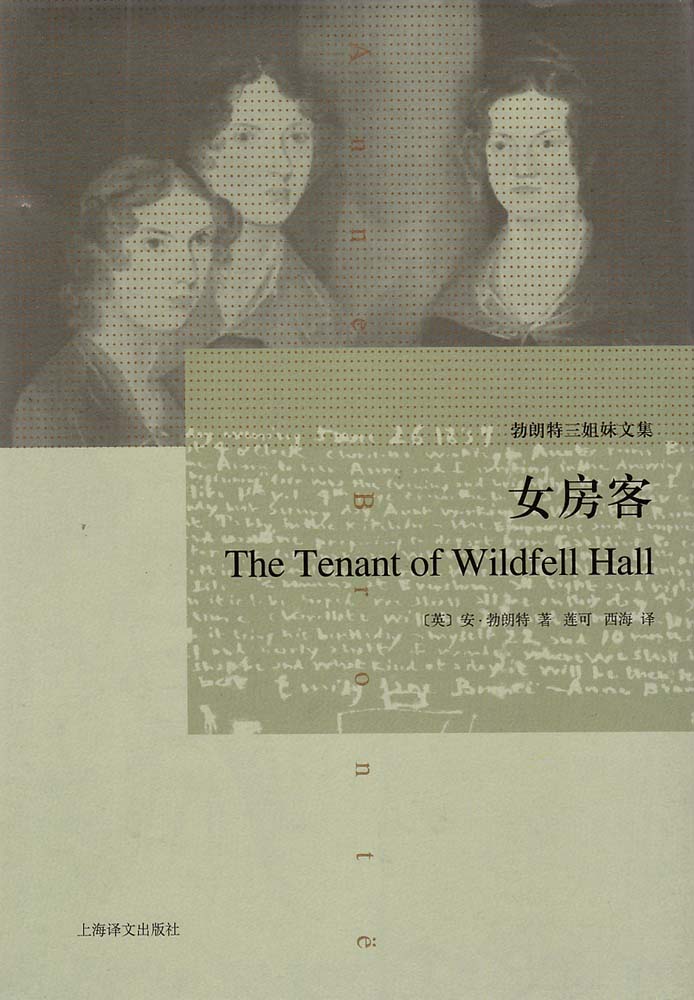 虽则我承认本书所取得的成功大于我所期望的,而且有几位出于善意的评论家所给予的赞扬也大于它所应得到的,但我也得承认,我同样地没有预料到它从其他方面会受到苛刻的批评,而我的判断力和感情都使我确信,这些批评是过分厉害而欠公正的。就作家的职权范围而言,他简直不能反驳他的审查员提出的论点,也不能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是,也许可以容许我在此发表一些意见。倘若当初我能预料到这些情况的话,我就会对那些抱着偏见来读本书,或者满足于匆匆翻阅一下便下判断的人,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原会用这些话作为初版本的前言的。 虽则我承认本书所取得的成功大于我所期望的,而且有几位出于善意的评论家所给予的赞扬也大于它所应得到的,但我也得承认,我同样地没有预料到它从其他方面会受到苛刻的批评,而我的判断力和感情都使我确信,这些批评是过分厉害而欠公正的。就作家的职权范围而言,他简直不能反驳他的审查员提出的论点,也不能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是,也许可以容许我在此发表一些意见。倘若当初我能预料到这些情况的话,我就会对那些抱着偏见来读本书,或者满足于匆匆翻阅一下便下判断的人,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原会用这些话作为初版本的前言的。
我写下面这许多页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逗乐读者,也不是要满足我自己的爱好,更不是为了要取悦出版界和公众;我希望说实话,因为事实的真相总是能向能够接受的人们传达它本身在道德方面的教训的。然而,由于那无价之宝往往隐藏在井底,需要有勇气的人潜入水中去取,特别是要去取的人得冒险投身于泥水之中,因之而招致的藐视和斥责可能会多于因找到了宝石而得到的感谢;这如同为一个不讲究整洁的单身汉的公寓套房承担清洁工作的女人,由于扬起灰尘而受到的责骂,往往会多于她完成清洁工作而受到的称赞。不过请别想象我自以为有能力去革除社会上的种种罪过和弊端,我只是愿意为如此良好的目标贡献微力而已,而且如果我果真能得到读者的注意的话,我宁可低声说一些有益的真话,也不愿讲许多好听的废话。
正如小说《艾格妮丝·格雷》中被指责为过分夸张的部分恰恰就是我用心临摹生活,力避言过其实的那些部分,同样,我发现自己在本书中被指责对某些情节“要不是出于对粗暴,就是对粗俗的一种不健康的爱好”而给予热烈的描写;而我敢说,即使是最爱挑剔的评论家看了这些情节,也不致比我描写它们的时候更感痛苦。我可能写得过于详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注意不再这样使自己或我的读者为此难过。可是当我们不得不写到罪恶和不道德的人的时候,我坚决认为最好要按他们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按他们希望让读者看到的面貌来加以描述。对于一件坏事的描述,采用最不引起人们反感的表现方式来写作,无疑是小说家能遵循的最合心意的方针。可是这种做法是不是最诚实,或者最安全的呢?应该向那些年轻而没头脑的旅客揭露人生道路上的陷阱和罗网,还是用树枝和花朵把这些陷阱和罗网掩盖起来,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好呢?读者啊!如果少一些这种对现实的审慎隐瞒——这种在没有安宁的时候低声说“安宁、安宁”的做法——那末,那些靠自己来从各自的经历中提炼出辛酸的知识的男女青年就会少犯罪、少受苦。
我不愿意人们以为我认为自己在本书中介绍给读者的那个不幸的无可救药的恶棍和他那几个放荡的伙伴的行为正是社会上普遍作风的一个样板。我相信没有人会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我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人。如果由于我的忠告,能够使一个轻率的小伙子免于重蹈覆辙,或者可以防止一个没头脑的姑娘像我的女主人公那样不知不觉地误入歧途,那末,这本书就没有白写了。同时,如果哪一位正直的读者看了本书后,从中获得的痛苦多于快乐,并且在合上最后一卷时,心中留下的是不愉快的感觉的话,那么我谨请他宽恕,因为这远非我的意图;下次我将竭力干得好些,因为我喜欢给人们以无害的娱乐。然而请理解我,我的抱负不会仅限于此——或者甚至仅限于创作“一部完美的艺术品”;我会认为把时间和天资如此消耗是浪费和滥用。我要将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份微薄的天资予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就算我能使人们得到娱乐的话,我还愿意尽力有益于人。而当我感到有责任说出不中听的事实时,我会靠上帝的帮助照样说出来,尽管这么做会给我的名声带来不利,并直接有损于我的读者和我自己的乐趣。
我再说一句就结束。关于作者的身份问题,我希望人们明白阿克顿·贝尔既非柯勒·贝尔,又非埃利斯·贝尔,因此请别把他的缺点归咎于他们。至于这是真名还是假名,对于仅仅通过他的著作来熟悉他的人来说,关系并不大。而且我认为,拥有这个姓名的作家不论是男是女(这一点,有一两位评论家自称已经发现了),也同样无关紧要。我乐意接受对我的诋毁,把它看做我对女性角色的正确描写的赞美;而且尽管我理应认为我的审查员们之所以如此苛刻,是由于他们怀有这一猜疑,我却无意予以驳斥,因为我相信只要是本好书,那末无论作者的性别为何,它仍不失为一本好书,这就够了。所有的小说都是,也应当是既供男性又供女性阅读而写作的,而且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容许自己写出确实使女性丢脸的内容,或者为什么一个女人写出了对男人说来是恰当而相称的任何内容就应当受到苛评。
1848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