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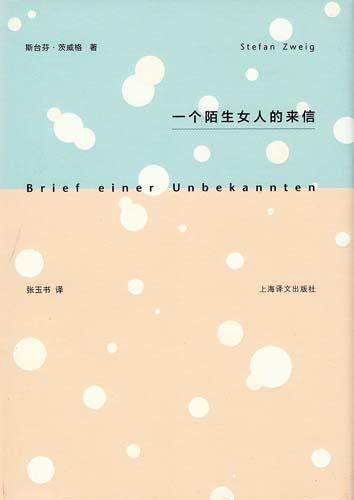 什么书给我们生命强度?什么书给我们生命高度?什么书在“地面行走”?什么书在“空中飞翔”?什么书让我们“犹如灵魂附体”……2012年的最后一个周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黎笙做客本报“爱上层楼”读书会,以自己阅读与创作的亲历亲闻,在华中师大武汉传媒学院与数百学子、书友书话生活,分享经典。 什么书给我们生命强度?什么书给我们生命高度?什么书在“地面行走”?什么书在“空中飞翔”?什么书让我们“犹如灵魂附体”……2012年的最后一个周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黎笙做客本报“爱上层楼”读书会,以自己阅读与创作的亲历亲闻,在华中师大武汉传媒学院与数百学子、书友书话生活,分享经典。
以下为黎笙讲述实录:
今天是读书会,我愿以我的阅读生活和创作体会与大家交流。最初感动我的一本书应该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读初中时我先看了电影,高中时读的小说原著,之前电影留下的影像烙印,让阅读常伴有画面、声音、色彩、人物表情等立体叠加效果,也使这种阅读成为一种独特奇妙的心灵体验。
最让我震撼的细节是:亚瑟在枪声中倒下,突然又从血泊中站起来,一手抚着胸,微笑着说,“你们打,朝这儿开枪,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意大利和他自由的儿子!”轰鸣的枪声再度响起,亚瑟倒在血泊中,湛蓝的双眼凝视着意大利的天空……读完《牛虻》后,我在书上写了一句话——“《牛虻》的启示:受苦而不诉苦”。
如果说《牛虻》给了我生命的强度,那么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则给了我生命的高度。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克里斯多夫的叛逆期,他对偶像的质疑,甚至连他最崇拜的偶像巴赫也逃不掉他的重新审视。克里斯多夫突然发觉巴赫不过是个沉闷、唠叨、痴迷于宗教的糟老头子……多年后他才重新肯定巴赫,但当时那样彻底否定,一锤子砸碎偶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好像随着克里斯多夫升华到人生的高峰,“一览众山小”。
在我从事写作的日子里,克里斯多夫的精神持续发酵,这对我1998年写作《中国股市启示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没有采访一个经济学家,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股市信息,一天读3本国内外关于股市的书。这本书完成后,受到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高度评价。
学以致用爱伦堡的蒙太奇手法 他把宏伟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结合,使之既有史诗的宏大格局,又生动传神
“文革”后,前苏联记者兼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给我印象很深。我四处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套六卷本,如获至宝。这部书是长篇回忆录,它为我们衔接上“文革”中一度中断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了解,为我补上了一堂生动的现代西方文化课。
作品介绍了几百位西方现代作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画家、雕塑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写人物寥寥几笔却分外传神。当过记者的他创造了一种电报文体,简练、形象、生动、信息量大且耐人寻味。这种电报文体使用大量的短句子。但它的短不是一般化的简短,而是一种快节奏的不断转换,包容性非常强,许多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扑面而来。比如他描写自己的红领带:“但愿在大街上,人们不至于把我的领带当成我的美学纲领”。
爱伦堡视域开阔,且善于叙写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方法是用蒙太奇,把宏伟叙事与细节描写相结合,使之既有史诗的宏大格局,又生动传神,令人难忘。比如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他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对情人在街头长椅上接吻。那是和平时代的最后一幕。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常用蒙太奇手法,如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治水人》,写了3个癌症病人共建一座大坝――患膀胱癌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患肝癌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患眼癌的长办主任林一山,3人亲自领导并倾注了建设葛洲坝的心血。这是中国治水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接着我又写了普通生活的两个细节——一位工程师的3岁儿子学会了自己洗澡;二是他家养的母鸡像鹰一样从6楼飞下觅食……如此两极镜头的运用,把大与小、高层领导人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相互衔接,在对比中鲜明地表达了建设葛洲坝工程的艰辛以及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努力“画”出人物之魂 斯通画的是工笔画,一丝不苟,是在“地面行走”;而茨威格是大写意,是在“空中飞翔”
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让茨威格荣登世界文学大师殿堂。其实茨威格写得最好的不是小说,而是人物传记。
将这位奥地利文学大师与美国现代著名传记作家斯通比较一下,不难看出,斯通画的是工笔画,一丝不苟;而茨威格是大写意,是泼墨。如果说斯通是在“地面行走”,那么茨威格却在“空中飞翔”。
比如斯通的名传《梵高传》,在准确写实上下足了功夫,甚至亲自丈量了梵高当传教士时教堂到矿井的距离,分毫不差;而茨威格要的则是生动传神,抓住主人公的魂。茨威格写《巴尔扎克传》花费了10年功夫:通读他的全部作品,而巴尔扎克仅长篇小说就有90余部;采访了许多与巴尔扎克有关的人物;找到几乎是力所能及找到的大量书信,以及巴尔扎克的债务证据,甚至巴氏的出生证明,将这些材料加在一起互相印证、类比,深入到巴氏的灵魂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