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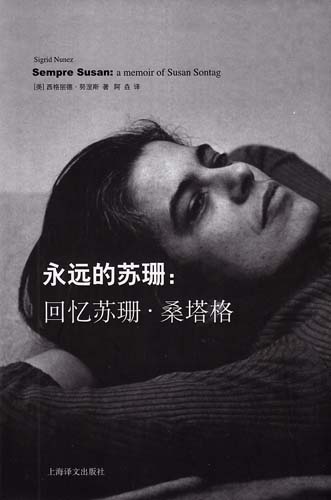 一 一
桑塔格在谈论已故的友人保罗·古德曼时曾写道:“我疑心,在他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他。”(《在土星的标志下》。编者注:本文所引桑塔格著作,均为乔纳森先生自译)。我们读完《永远的苏珊》,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她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苏珊。
读《永远的苏珊》这本书,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一本回忆录,它是否可靠。我的结论是,非常可靠;不仅可靠,有些时候,努涅斯的笔甚至有“颊上添毫”的妙处。
2012年4月,桑塔格日记的第二卷《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日记与零札 1963-1981》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编辑出版,当中只有一处提到了努涅斯。时间为1976年11月12日,记录的是桑塔格自己对努涅斯讲的一段话:“纤细的感性迎头撞上卑劣、无情、令人沮丧的世界,这可算不上什么题材。去给自己找一场竞技赛吧。”努涅斯在书中提到犹豫了几个星期才把自己的习作拿给桑塔格过目,上面这段话恐怕就是在此时讲的。
日记第二卷与《永远的苏珊》可印证的地方不少,这里只举一处为例。努涅斯的书里讲,桑塔格抱怨搞批评太折磨人,总想写小说,说:“我讨厌那么辛苦地工作,我想要歌唱!”而在1977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桑塔格写道:“我想写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想要歌唱。”这五字宣言的记述,可谓分毫不差。
当然,这些印证还只是形式上的精确,更令我们对《永远的苏珊》内容确信无疑的,是它跟日记一起呈现了一个比我们以往知道的那个桑塔格更脆弱的女人、情人及母亲。
二
不管是日记,还是回忆录,都无异于桑塔格的精神征候集。那些对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女批评家写的东西提不起兴趣的人,正不妨将以下所说的权当一段有关普通人的心理故事。
任何在世界上稍微做出那么点事业——哪怕是蜗角功名也好——的人,迟早都要在自己内心的天平两端放上这样两件东西:“我能做什么”和“我想做什么”。有些人,说是幸运也好,说是不幸也行,在他们的一生中,根本没机会把这两件东西掂量清楚,可以略过不谈,可那些脑子还算灵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征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地点,到了那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暗叫一声“不好”,明白这世上有些事自己恐怕是干不了了。在这群“顿悟”的人里头,最理想的,当然是他能做的恰恰是他想做的或者他能做的里有他想做的,世上一多半伟业都是这样天平摆平稳了的人干出来的。剩下的,就都是“我想做什么”那头高,“我能做什么”那头低的了。要是一端永远高高在上,那这人就一事无成了,可偏偏这样的极少,因为前提是他脑子还算灵光,现实总会矫正他的,头破血流了,一摸,心下也就明镜似的了。更多的是天平老晃悠,不稳定平衡,心气压不下来,实力提不上去,这就是所谓纠结拉扯了。桑塔格始终都没能把她那架天平调平。但得补充说一句,世上余下的那一少半伟业,正是这些内心纠结拉扯的人做出来的,纠结拉扯未见得就做不成事情。
桑塔格是对自己有明确认知的人,在1966年1月4日的日记里,32岁的她写道:“我不够有雄心,因为我总是自满。五岁时,我对(管家)玛宝说我要得诺贝尔奖。我知道我会成就声名。那时生活像是坐电梯,而非爬楼梯。后来我知道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够聪明成为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萨特或西蒙娜·薇依那样的人。我的目标是作为弟子追随他们;在他们的水准上工作……但是,我并非天才。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既然不是天才,还怎么“在他们的水准上工作”?
到后来,桑塔格也坦然向外人承认:“如何超越自己,是我作品中埋藏最深的主题。”(《苏珊·桑塔格对话录》)桑塔格写的评论广受好评,她写的小说常遭冷落,可她一门心思惦记着写小说,因为做自己能做的还有什么意思,做自己想做的才叫“超越自己”。1978年,她写本雅明的一段话也等于夫子自道:“自我是一个有待破译的文本。自我是一个有待构建的工程。构筑自我、构筑其作品的过程永远太缓慢。人,永远在自我拖欠之中。”(《在土星的标志下》)
“超越自我”,本身就像是矛盾修辞:假若自我是可超越的,那超越它的又是谁呢?不还是自我吗?同一个自我完成了这件事,可见并无所谓超越发生。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超越自我的尝试本身正是创造那一少半伟业的努力。天平翘高的一端每一次下压,都带动了一次破译,带动了一次构建。假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胜业,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说,她燃烧的充分程度丝毫不低于她列举过的那些天才?她完成了一个批评家所能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