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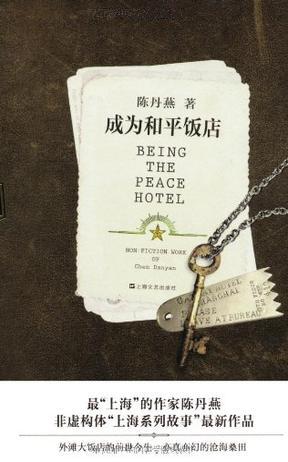 “到了三十岁,就自杀吧。 ”少年时代,陈丹燕曾对她的闺中女友这样说。 “到了三十岁,就自杀吧。 ”少年时代,陈丹燕曾对她的闺中女友这样说。
“在少年的心目中,一个人过了三十岁,可谓老朽,生命的灵光一定已经熄灭了。少年时代激烈的心情里,不希望自己如茶花那样活着,谢在枝头上,像一块朽烂的红布。 ”
可是,时光转瞬即逝。陈丹燕度过了她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不仅完成了多部著作,也走过了无数旅程。不久前,陈丹燕将其写作至今25年来的散文进行了编辑整理,出版了“阅历三部曲”。在后记中,作家如是感叹:“五十岁时在北极见到了神性的自然,突然得到了自然的精神抚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了越来越宽广的道路。我觉得每一条皱纹都来得不容易,每一根白发都有变白的理由。原来,生命的成熟是这样完成的。 ”
陈丹燕私下披露,现在自己仍与少年时代的女友时时见面,彼此望着对方皱纹中的笑影时会惊叹,原来大家都没自杀,“转头一望,发现三十岁时还太年轻和潦草”。
成长
趁皱纹和白发还很新鲜的时候
记者:梳理25年散文的过程,你有一个怎样的感慨?
陈丹燕:散文中总是有不少自己在生活中即刻的所见所闻,当时觉得是获得一时倾吐之快。在修订两本旧作、编辑一本新作的时候,发现这些看似已经忘记了的细节与场景,人物与时代,重新回到眼前。这种时光世事交融流逝的感受,我想就是一个人突然回顾自己生命的过程。
记者:据说结集中你删了不少旧作?哪些作品回头看时,不再入你的“法眼”?
陈丹燕:并未大幅删减,但的确是有些作品不再收入书中,时光会淘汰一些作品。其实自己的作品,对自己来说,怎样都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但散文集并不是作品回顾,还是要有取舍。
记者:这套《阅历三部曲》,在写作时间上,跨越了你生命中30、40、50岁这三段最重要的时光,书封分别用了三张照片来对应。你能否用文字分别描述一下,你站在30、40、50岁时,对人生有什么不同感悟?
陈丹燕:封面上的是三幅画像,看自己的脸在岁月中的变化,特别是将两张不同时代的脸拼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想到自己生活中那些寂静的写作的日子。什么声音也没有的,窗外阳光灿烂的,自己一个人在寂静中与纸上的世界搏斗,所谓甘苦自知。三十岁,就是写《唯美主义者的舞蹈》时,我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心情,建立自己的文字系统。到四十岁,写《上海色拉》的时候,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份认同,关心自己所在城市的身份,探索上海的历史,我的视野由于大量的旅行和在大学的演讲,开始变得开阔。四十到五十岁的这个阶段,还写了《蝴蝶已飞》,这个书名来自于我参加孩子大学毕业礼时,看到蝴蝶纷飞时写了一小段字。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许多变化,我的亲人们渐渐离去,能告诉我小时候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我母亲的责任已经结束,从此要做朋友,而所谓做朋友,就是不能关心太多、照顾太多,要旁观。我写了二十年的非虚构的上海故事要告结束,我发现非虚构已经成为我写作的重要文体,我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也许我要启程尝试新的领域。自由回到我的面前。这次似乎我面对的是平静的大海,已不是湍急的江河。我渴望跃入大海之中。
记者:对于成长,你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每一条皱纹都来得不容易,每一根白发都有变白的理由。好像交学费那样,你交出青春,换得智慧。”在面对年龄时,为何你可以做到如此坦然?岁月带给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陈丹燕:我相信每个人的获得不同。我现在,趁皱纹和白发还很新鲜的时候,能说得出它们的来源,它们在带给我外表变化的时候,还有一些藏入心中。在编辑这三本散文集的时候,我数过它们,觉得在内在,它们留下了智慧,还有力量。我觉得不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现在都比从前有能力分析事物。平静自己,安慰与支持别人,这让我觉得很安慰。
亲情
我和女儿还能如此沟通对生命的理解
记者:担纲“阅历三部曲”封面设计的是你女儿陈太阳。你对女儿的设计打多少分?有一天,她会不会也成为“写二代”?
陈丹燕:陈太阳的第一个方案是她眼睛里写作中的母亲,从一个较低的视角,看到母亲在写字桌前的背影,渐渐升高。这是本能的回忆。小时候她喜欢从后面爬到椅子上来,玩我的头发,和我说话。后来她理解我对自己面容的变化觉得很光荣,就改用面容的变化来做封面的重要元素。三本书的封面,六个块面可以首尾相连,最后成为岁月流转的象征,这是她的体会。我们谈到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我觉得生命中的能量、理想有时并没有消失,那些看似消失在时间中的感情,有时会完好地回来,那就是一个人生命中不会失落的部分,自己的坚持。她用一个等边三角形来表达了我的想法,让我觉得欣喜,更为欣喜的是,我和自己的孩子还能如此沟通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她能帮我表达出来。这是写作附带而来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