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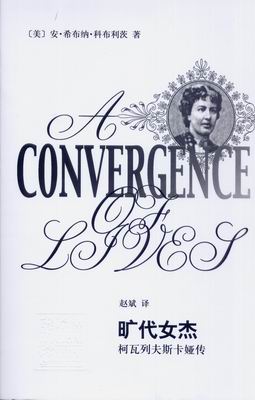 □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 吴 慧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前段时间,你赠了《辞海译丛》首批四部科学文化类译著给我。这套书的文化品位和装帧设计是我所喜欢的。因为研究兴趣的关系,我首先阅读了其中的《旷代女杰——柯瓦列夫斯卡娅传》。在课堂上,学生们常常抱怨译著读起来十分晦涩。殊不知,好的译著,行文流畅,读起来同样可以让人不忍释手。这部《旷代女杰》,便可算是我近来读得最轻松也最入迷的译著了。
无疑,这本书的作者对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性别与科学研究有一定的了解。她想做的是提供一个跨文化的女科学家案例,并以此补充或纠正上述研究方面的一些既有观点。在她的眼里,作为居里夫人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女科学家——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的故事表明,做女人和做数学家一点也不矛盾,在科学研究中,女性同样可以获得极大的愉悦,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
■ 我用了两个晚上把这本传记读完了。自卑、敏感、早慧、孤独、柔弱、固执、积极,这组词大致能勾勒出索菲娅大致的形象。这两年我受到你的影响,也常常会想想女科学家的双重身份,她们遭遇的问题,应该被当做女性对待的时候,她们可能受到“科学家”气质的诟病,在“科学家”身份时,被关注的却是“女性”身份。所以女科学家,需要更丰富的生命和一点运气。不过我这想法,会受到女性主义的诟病——请先独立并且自信。好吧,让我们很独立自信地来看看索菲娅的一生。
早慧,幼时不大跟同龄人打交道,自学认字,爱好阅读,喜欢文学,有数学的天赋,为了获得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用和柯瓦列夫斯基假结婚的方式出国学习,写出博士论文,能力得到导师的肯定和青睐,在数学世界里获得成就。然而她的一生怎么可能是这些干涩的词句就能够展开的。
□ 的确,“双重身份”常常是科学界女性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并非因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生物学事实所导致。实际上,正是社会性别文化包括科学理论本身常常将女性塑造为科学的对立物,促使这二者在气质上看起来截然有别甚至互不相容。试想,一个柔弱敏感、易于感情用事的女人,怎能在一种要求从业者身心强大、头脑时刻保持冷静和理性的事业中获得巨大成功呢?即使偶尔有之,这样的女性一定是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优秀品质,且这个品质必然是适合从事科学但却远离小女人气质的。
该书作者之所以详尽叙述了索菲娅的少年生活、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尤其是她在文学上的造诣,无非是想表明一个热爱文学的女孩同样可以学好数学,甚至成为一流的数学家;尽管现实百般残酷,她精彩丰富的一生仍足以表明,在爱情和数学之间、在女性气质和科学气质之间所作的人为划分是可以被消解的。
■ 学术简历和曲折的情感经历,是两条贯穿起她一生的线索。但确确实实,它们是两条线索,在该书的110页,这两条线索有个交点。
1874年,索菲娅和丈夫从欧洲回到俄国。深受对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歧视和对欧洲学派的偏见,索菲娅求职无门,加上父亲的离世以及经济上受到的牵制,夫妇二人从研究生涯里自我放逐,经营起另外一种世俗的日子,也改变了之前假结婚的相处模式。朋友们发现索菲娅的行为变得更“女子气”和更有依赖性。他们甚至感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婚姻成功。而索菲娅的丈夫也鼓励她这样,让她感受到对自己的完全的依赖。这一时期的女科学家,投身沙龙、剧院,过起了文艺的生活。
为女科学家高兴吧!她也擅长这类社交。为女科学家难过吧!女性对实现不了的情怀的失望一如失业对男性的打击。理解女科学家吧!用心经营的东西被漠视,她以沮丧和感情用事来宣泄。1877年的索菲娅说:“让我只与数学接触,我将会忘掉世界上其他一切事情。”
□ 有趣的是,你提到柯瓦列夫斯卡娅夫妇人生中的那段充满商业和文艺色彩的生活片段,恰恰让读者发现,有时候男性更懦弱、更容易自我放弃,而女性却可以在挫折中坚强地重新开始。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随意地贴上性别标签。理性或非理性,坚忍或懦弱,适合从事科学或不适合从事科学,这些和男性与女性并不能想当然地画等号。
实际上,不能随便贴标签这事儿,正是作者反复想要强调的。作者说她要提供一个跨文化的性别与科学的故事,目的也是想说科学领域的性别偏见并非处处都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言的那样。索菲娅在数学世界里得到过男性导师和男性同行们的无私帮助,她遭遇的困境更多是来自社会上的性别歧视文化。不过话说回来,仅此一点仍未真正突破西方女性主义的科学叙事;但力图揭去形形色色的固定标签和推翻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这事儿作者做得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