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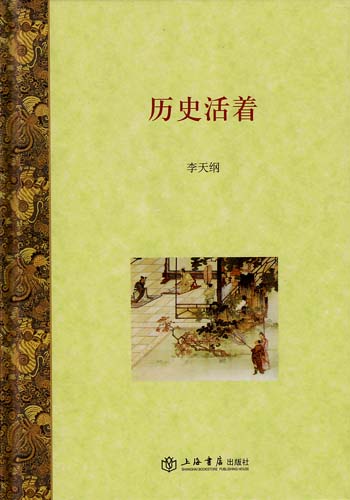 8月22日下午,沈昌文、陆谷孙、葛兆光、戴燕、陈子善、叶扬、孙甘露、毛尖、李天纲、沈双、俞晓群、王为松等学者和出版人齐聚2666图书馆,举行“海上文库”、“海豚文库”出版座谈。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海上文库”和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书馆”秉持“小而美”的理念所出版的这两个小精装系列,一本一本出下来,渐成风景。来自京沪两地的这两套书的策划者和作者,因为上海书展得以聚在一起,于是有了这次座谈会。 8月22日下午,沈昌文、陆谷孙、葛兆光、戴燕、陈子善、叶扬、孙甘露、毛尖、李天纲、沈双、俞晓群、王为松等学者和出版人齐聚2666图书馆,举行“海上文库”、“海豚文库”出版座谈。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海上文库”和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书馆”秉持“小而美”的理念所出版的这两个小精装系列,一本一本出下来,渐成风景。来自京沪两地的这两套书的策划者和作者,因为上海书展得以聚在一起,于是有了这次座谈会。
沈昌文(出版家,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我大约六十年前离开上海去北京,十九岁的我当时在北京算“上海帮”。小学毕业,中学上了一年,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是“小赤佬”,有点受歧视。在上海时,读的多是小报,敬佩的文化人也是小报作者,现在还记得当时每天追看的情形。读得最早的小说是苏青写的,因为苏青是我们宁波老乡,当时我知道苏青的爱人是做律师的之后就更佩服了。小报作者里最喜欢的是“牛马走”,上海汪伪时期的电影局局长,汪伪倒台以后他日子就不好过了,成天打扑克过日子。我是做小赤佬伺候别人的,所以我伺候他打扑克时,一边在旁边念《古文观止》。他看我老在念《五人墓碑记》,就说我没出息,让我少念这本书后面的文章多念前面的文章,前面的文章更好。点点滴滴间,我受到他的教育很多。在这样的海派文化圈子里长大后,我慢慢懂了什么是真正的海派文化。
这几年老有一个想法,看到韩正市长去台北,觉得台北和上海合作很好,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海派文化,集合有识之士和海内外华人文化各种优点、长处的新海派文化。很希望在座的陆谷孙、陈子善带头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新海派文化,把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优点都集中起来,再介绍、出书。我乐观展望,今年八十岁看到两套书出了近一百种,希望九十岁时来上海能看到这样的书有一千种,使我们这些文化贫乏的人能受到教育。这个观点我过去和龙应台、新井一二三等港澳台和海外作家也谈过,大家对新海派文化的概念非常赞成,而且觉得应该以上海为中心。
今天凑巧“海上文库”、“海豚书馆”都在一起,可说是太平洋和大西洋合流。
王为松(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我接着沈公的话表态,只要陆谷孙、陈子善两位主编肯编,我们就出一千种。
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说起海派文化,“海上文库”在上海出版,自然海派味很浓;“海豚书馆”的出版地虽然在北京,但收录的多是上海学者、作家,也是海派味道。我们策划“海豚书馆”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年觉得辽教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有些书目做得不好,一次在一家上海菜馆吃饭和沈公聊起这个,他说可以找陆灏继续做,于是就有了再一次的“桃园三结义”。
陆谷孙(复旦大学教授):这一年,对书展来讲,是轰轰烈烈又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是浑浑噩噩又一年。去年还为郝明义策划的大块文化系列讲座讲过莎士比亚,今年书展却不想出来,是陆灏说你一定要出来才出来的。不想出来,是因为躲在洞里觉得很舒服,不想和喧嚷的世界过多接触。
你们看我这满头白发就知道,我已经变得很悲观了。比如消极情绪表现在不整理书房,别人借去的书不还,看的多是借别人的书。法郎士讲过,一个人到最后,书橱里只有借来的书。我有点体会了。“海豚书馆”刚出版我翻译的爱德华·李尔的《胡诌诗集》,曾被人说成“吃饱饭没事做”,但现在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宏大叙事都放下,做些好玩的事情。现在语录体的微博也是这样。常想起“一”和“多”的关系,以为自己是“一”,哪里“多”了就围剿,是容忍不够多的表现。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大家心思都不沉静,痴迷于信息和语录而不是知识,学生以后的发展让人忍不住打个问号。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尔值得介绍给中国这个闹哄哄的社会。李尔出身低微,和查尔斯·兰姆一样为伺候姐姐终身未婚,自己身体还有疾病,但他却很笃定,写了那么多好玩的诗。前次去英国,没想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里居然也有他。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我觉得小开本的书都挺好的,今天就在这里给小开本追溯渊源吧。郭店楚简有一种很小的简,是用微博式、格言式的语体记录临时对答和应酬等内容,相比其他很长的简,这种简装在身上就好,携带方便,这恐怕是最早的小开本了。到了敦煌文献中有一种随身宝,宋代以后印刷发达,又有巾箱本,都携带方便。这些都可视为小开本的前身,都是随身携带的便携知识。现在iPad等电子阅读设备显然更方便,小开本靠什么维持?除了内容、装帧做得更精致,也要想想其他贴合时代气息的创意。
戴燕(复旦大学教授):小开本带在路上看很方便。好多次要出门,摸来摸去觉得带什么大书都不合适,还是带上小书。就是精装的装帧质量不够稳定,有时会脱落。在这个乱哄哄的时代,你们能坚持慢慢做,一本一本出,很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