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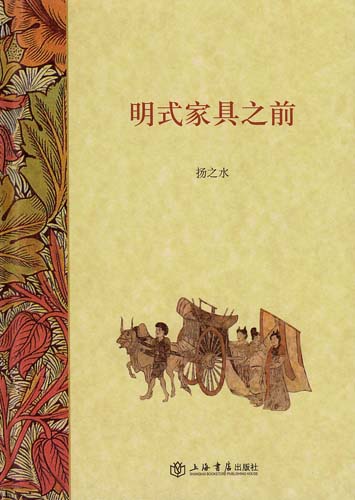 “两宋是养‘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一个黄金时代。士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山水、田园、花鸟,以茶以香为语汇,用想象和营造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他们在这里收藏情意也收藏感悟,并在感悟中化解尘世中常会有的种种失意。” “两宋是养‘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一个黄金时代。士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山水、田园、花鸟,以茶以香为语汇,用想象和营造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他们在这里收藏情意也收藏感悟,并在感悟中化解尘世中常会有的种种失意。”
春明读书,胜日寻芳,都是闲作文章的好题材,旧都过去无论南京北京,冬寒尚未脱尽,郊外已见携酒踏青的行迹,暖风扶晚,丁香醉人,卷书卧柳,意态庸倦,这本是宋徽宗《听琴图》的景致,扬之水引来作《明代家具之前》局部一角“鹤膝棹”的物证,“鹤膝桌子的形象,五代画作中即已出现,如河北曲阳县王处直墓壁画。又有故宫藏酒题唐卢棱伽实为宋人之笔的《六尊者像》,宋徽宗《听琴图》,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又宋《人物图》。而由《人物图》尤其可以看出它的布置。”这情景当为郊外游宴所设,此是宋时风光,扬之水在《宋代茶床》一节说“茶床在使用在两宋依然很流行,式样也没有太多变化,但功能却日益明确,即专用于摆放茶酒食。”而“出游而以茶床相随,其情景也可以援画为证,”这茶床发展到“由席坐向高坐具过渡的过程中” 出现了鹤膝棹,可见宋时家具富含山野意境。
扬之水《明式家具之前》开篇便说:“两周家具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中的第一个高峰”是以文献为征,而作“认定它的名称和性质。”这里能够认定和谈论的家具不多,作者所举坐卧用具,多从《诗》里得其名称,“能够用文献与实物互证而支撑起来的先秦家具史,以两周时代的材料最为集中,也相对可靠。”这时大约有凭几、床供坐卧,置物之具有俎、禁等几样,皆与祭祀崇拜相关联,“然而它注入了礼的内容之后,即要以制作的精美和陈设的位置来维系一种高贵的姿态,种种奢华便好像都是为了一种精神而存在。”正是作者文献与实物互证考据方式,又因作者曾作诗经名物考证,对先秦文献研究深具功底,如:“屏风之称不见于《经》,它出现在先秦经典中时通常名之为‘扆’或‘依’,又或用鸟羽装饰得华丽而称作‘皇邸’。不过后之史籍述前朝故事,已经自称作屏风,如《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云其‘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论述周详,虽那些家具因离我们的时代太远而难以对其产生兴趣,但若静下心来读扬之水的文辞,颇耐咀嚼。
以读者的角度来读,《明式家具之前》里《行障与挂轴》与《唐宋时代的床和桌》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关联较多,又因所谈家具常于绘画中见到,书中文字与插图对照着阅读,可引发出视觉的趣味来。譬如:“《列女传》是屏风画的传统题材,《列女传》本来即为图画屏风而作。”说来读者多可理解,但却未知《列女传》之原由,经作者讲述,方始明白。再因绘画可作文字描述,“但以其衣带飘扬的轻倩婉丽特别能够显出婀娜,而为各种表现艺术所吸纳,成为刻画古代女子形象的一种通行的艺术符号,直到唐代,创作敦煌壁画的民间画手对这一表现形式依然是熟悉的。”这里谈论绘画里的仕女衣裾,给人“吴带当风”的感受。回到家具这个话题上:“作为接近完成的过渡期,宋代家具名称与功能的对应逐渐趋向细致和明确”,而其他艺术也如此,绘画之外,词曲、瓷器等,都走向细致与完美,家具则为明代开启简约风尚,宋代实为先导。再回到扬之水对宋代绘画的叙述,已超越唐代的故事写意而为抒发意境:“对于士人来说,一桌一榻或一把交椅,便随处可以把起居安排得适意,可室中独坐,也可提挈出行,或留连山水,或栖息池阁。可坐可卧,闻香,听雪,抚着风的节奏,看花开花落。”安逸如此,足令后世神往。“当然这是宋人用诗和画构筑起来的田园之思,其中自然很有理想的成分,但此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真实,是椅子和桌终于结为固定组合,在长久的演变过程中完成了家具陈设的一种新格局。”作者将思绪牵回到家具上,犹如春季里手中的风筝,收放都随心愿。
这些论述多可看出作者思想,即明代以前中国的艺术已具备可称辉煌之势:“两宋是养‘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一个黄金时代。士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山水、田园、花鸟,以茶以香为语汇,用想象和营造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他们在这里收藏情意也收藏感悟,并在感悟中化解尘世中常会有的种种失意。”气韵与风骨可支撑起时代特征,而唐宋元明清这种连贯的艺术关系,以及各自独立的气韵与风格,多在相互穿插中各领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