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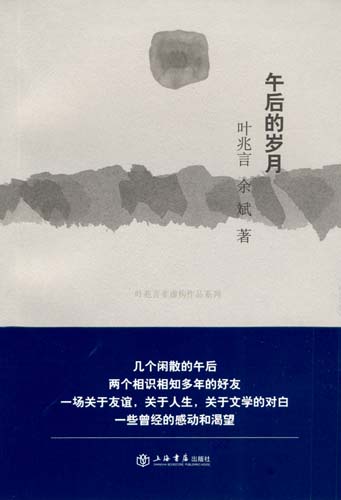 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二十多种散文随笔集,可谓运笔如飞,精猛奋进,大有著述等身之势,彰显文坛常青树之姿;相比之下,他的小说创作反而退居其次,叶兆言因此而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当前,诸多文坛名家往往忙于经营小说、影视,而视散文为末技小道;更有一类不乏才情禀赋的散文写手,把散文刻意经营成为“心灵鸡汤”,满足于以小情小调取悦庸众。在此语境下,叶兆言的创作倾向值得关注。 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二十多种散文随笔集,可谓运笔如飞,精猛奋进,大有著述等身之势,彰显文坛常青树之姿;相比之下,他的小说创作反而退居其次,叶兆言因此而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当前,诸多文坛名家往往忙于经营小说、影视,而视散文为末技小道;更有一类不乏才情禀赋的散文写手,把散文刻意经营成为“心灵鸡汤”,满足于以小情小调取悦庸众。在此语境下,叶兆言的创作倾向值得关注。
印象里,叶兆言不纯以才情取胜,而似乎更以耐心和定力见长,步履稳健,安于寂寞,朴实坚韧如骆驼祥子,被公推为文坛马拉松健将。叶兆言的文字并不令人惊艳,却耐看耐品。这些年,叶兆言的散文随笔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其下笔长短随意,小大由之,收发自如,犀利俏皮,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我手写我口,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叶兆言的创作实践证明,好文章完全是可以练出来的,只需下得苦功夫,坐得冷板凳,就不必迷信于所谓的天才和基因;叶兆言的成功也充分验证了,小说家致力于散文随笔并非不务正业,做得好,同样能够别铸辉煌,衣锦还乡。
“文”或散文,向来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至“五四”则迅速成熟。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使得散文的文体定义宽泛有加,“五四”迄今,一直聚讼不休。习惯上,人们把韵文以外的一切文章统称散文,包括杂文、随笔、特写,以至日记、演讲录、回忆录、书信、创作谈、札记、随想录等。显然,叶兆言的文本,更近于“广义的散文”。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俨具层峦叠嶂、千手千眼之势,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糅合平民语调、文人笔墨以至小资情调,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景,理趣、智趣、谐趣、灵性兼备,当得起平民化的“满汉全席”之誉。叶兆言的创作是散文写作的异数,也是散文写作的常数:本质而言,散文,的确应该是“杂文”———博杂之文。
“一想到刘半农,我的脑海里立刻就冒出大脑袋瓜和鱼皮鞋。”(《刘半农》)“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这是怎样栩栩如生的小说家语言?作者笔下功夫,大有折冲樽俎以一敌百之势。“高尔基的作品仿佛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仪仗队一样浩浩荡荡陈列在父亲的书橱里。”(《革命文豪高尔基》)“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春梦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从中尽可见出才情、识见、韵致、境界,见出元气淋漓驳杂包容。尤其这类连珠妙语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可谓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色。
“有人形容中国地图像一只引颈高歌的大公鸡,江苏就处在公鸡凸出的那块胸脯上。”十五万字的《江苏读本》着意点染江苏的地域文化,笔法矫夭腾挪,活灵活现。“巍巍钟山也就四百四十八米,由东向西,仿佛一把宝剑劈向南京城,高高拱起的钟山就是刀把,然后那些断裂的一截截刀身,插在了泥土里,形成了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高地小山丘。它们其实都是钟山的余脉……”笔力熨贴跳脱,动静相宜。小说家散文特有的生动形象活色生香,惊人的事象捕捉能力,确让那些读惯了一本正经的“职业散文家”作品的读者大为惊奇,大感受用。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随笔中的精华所在。朝花夕拾,旧事重提,在这类文本中,无论何等了得的对象,叶氏皆能以平民视角出之,身手之佳,有如探骊取珠。总体看,叶兆言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外被锦绣,内含翠羽,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几臻炉火纯青。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藉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
叶兆言从个体视角出发,讲述近现代史上诸多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随性随心而又考证有据,笔下氤氲着沉静的士子气,弥散着温馨与苦涩。叶兆言写人记事,往往发人之所不发,言人之所讳言,从生活琐事中品味现代文化名流的独立人格与个性,呈现出厚实庄重之格局。因了叶兆言的特殊家世,这类掌故史迹由他口中道出,格外真切,也格外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