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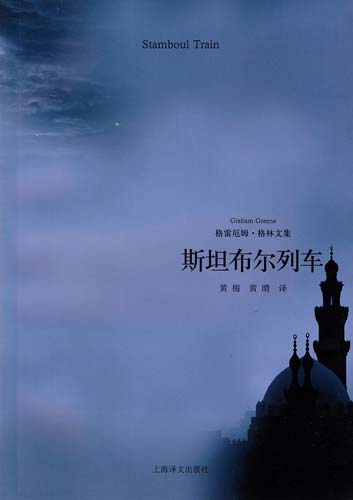 文学作品常借用长途旅行的时空坐标,将一个个移花接木的故事叙述得妙趣横生。因为人们客游异国他乡的行脚,与人生命运的遭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两个素昧平生者行色匆匆中的一个照面、一番交谈、一趟邂逅,乃至一夜缱绻,都可视为人生漫漫长途中的某次机遇变幻的袖珍版本。况且旅途中的景色风光,无论夕阳薄雾、抑或轻霜寒雪,又是小说家描摹相貌个性,渲染心理活动,大可信手拈来、任意涂抹的绝妙色彩。无怪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雷厄姆·格林文集”中新出的《斯坦布尔列车》,将一个追捕与逃亡的故事,安置在这列穿行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从奥斯坦德,经过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洲际列车上讲述。 文学作品常借用长途旅行的时空坐标,将一个个移花接木的故事叙述得妙趣横生。因为人们客游异国他乡的行脚,与人生命运的遭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两个素昧平生者行色匆匆中的一个照面、一番交谈、一趟邂逅,乃至一夜缱绻,都可视为人生漫漫长途中的某次机遇变幻的袖珍版本。况且旅途中的景色风光,无论夕阳薄雾、抑或轻霜寒雪,又是小说家描摹相貌个性,渲染心理活动,大可信手拈来、任意涂抹的绝妙色彩。无怪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雷厄姆·格林文集”中新出的《斯坦布尔列车》,将一个追捕与逃亡的故事,安置在这列穿行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从奥斯坦德,经过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洲际列车上讲述。
这是英国著名作家格林自称为“消遣小说”的书,他由此书而一举成名。书中,一位流亡英国多年,乘车赶回故国准备发动革命的革命家津纳医生,正躲避着军警的追捕,却遇到了为获得每周四英镑加薪而不择手段猎奇的女新闻记者梅布尔;梅布尔原本是来采访车上那位装腔作势的作家萨沃里的,可她为了识破津纳医生的身份,竟然撬开他的行李箱……发生在这阴冷时节的旅途中的故事、人物,不仅是逃亡与追捕:有一位惹人注目的俊俏的歌舞女伶科洛尔小姐,因为买不起卧铺,遭到挤在身边的男乘客性骚扰无可奈何;富裕的犹太商人迈亚特虽然时不时地都在心中盘算自己的葡萄干生意,但对科洛尔小姐的处境萌生怜悯而让她睡自己的卧铺包厢;科洛尔用一夜情支付迈亚特的慷慨;因为偷盗被发现铤而杀人的歹徒约瑟夫,也装模作样地上了车,并马上又开始算计津纳医生的钱财……
与其说格林在《斯坦布尔列车》中苛刻地打量着小说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层次分明的剖析,比较着邪恶、残忍、刻薄,或者是用意不良的愚蠢,不如说格林是用宗教徒的虔诚,扫描着尘世间人们生命行程中罪孽的生成与赎罪的踯躅。他作品里的人物往往置身于异国他乡,陷身于焦躁不安的疏离感中而不时左盼右顾,掂量自身的精神价值。自然风光的变幻、日常生活的琐碎,看似如同漫不经心的顾盼一瞥,却成为格林笔下的细节,用于镂刻、描摹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悸动。在细节中,读者似乎可以看到被诱惑的欲望正升腾于迷漫薄雾中,魔鬼在狞笑、心灵在挣扎。
格雷厄姆·格林从不蘸着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抹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是他认为:如果说人性有色彩,那决非是黑白分明的,而是黑白相互渗透的灰色。格林的出色在于他美妙地区分那灰色的种种不同层次。在他称为“严肃小说”的散发度假胜地喧嚣声的《布赖顿棒糖》、弥漫越南战火硝烟气的《文静的美国人》中,他让故事主人公的道德观念倍受煎熬;在他称为“消遣小说”的渲染间谍生涯和战云阴霾交集氛围的《密使》和《恐怖部》中,他又用女性的深沉爱情,拯救几乎陷于绝境的男主角。所以他的小说,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格雷厄姆·格林的多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斯坦布尔列车》、《布赖顿棒糖》和《文静的美国人》等,因此可见,他的黑、白、灰三色,完全可以勾画大千世界人生百态的绚丽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