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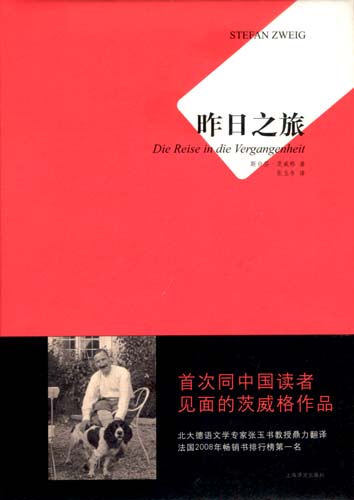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之前,《昨日之旅》这篇小说从未全文发表。它初次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奥地利当代艺术家协会文集》(维也纳,一九二九年,第一年卷),篇名为《一篇小说的片断》,与原文有出入。同样的片断于一九六一年,作为茨威格协会的《第二部特别出版物》,在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协会出版社出版,主编是埃里希·菲茨鲍尔。又经过二十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小说才得以全文发表,收集在克努特·贝克主编的茨威格小说集《火烧火燎的秘密》里,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二○○八年十月,法国格拉塞出版社首次发表了这一小说的法文译本,译者是巴蒂斯特·图卫雷。可见这篇小说面世的过程的确曲折漫长。 一九八七年之前,《昨日之旅》这篇小说从未全文发表。它初次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奥地利当代艺术家协会文集》(维也纳,一九二九年,第一年卷),篇名为《一篇小说的片断》,与原文有出入。同样的片断于一九六一年,作为茨威格协会的《第二部特别出版物》,在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协会出版社出版,主编是埃里希·菲茨鲍尔。又经过二十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小说才得以全文发表,收集在克努特·贝克主编的茨威格小说集《火烧火燎的秘密》里,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二○○八年十月,法国格拉塞出版社首次发表了这一小说的法文译本,译者是巴蒂斯特·图卫雷。可见这篇小说面世的过程的确曲折漫长。
这篇小说的情节,时间跨度很大,从第二帝国(即威廉二世执政的德意志帝国)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法西斯上台的前夕。在贝克的小说集里,这篇小说题名为《现实的阻碍》,说明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对普通人命运的巨大影响。
小说的情节是出身贫寒、才气过人的化学博士路德维希和他的老板枢密顾问G的夫人之间,苦苦相恋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当时,有名望的企业家也和政治家一样,拥有“枢密顾问”的称号,以示地位显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年轻的博士被枢密顾问派到墨西哥去开采矿石,创办分厂。光阴荏苒,终于熬到归国还乡的时刻,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是,这对朝夕期盼的恋人,天各一方,音信被阻。博士不耐孤寂,也不信战争能迅速结束,于是在大洋彼岸结婚生子,建立家庭。不料,大战在四年后突然结束。他获悉枢密顾问已经去世,夫人安然无恙,于是旧情复萌。他利用出差回国的机会,造访夫人,重游海德堡,寻找往日的踪迹。然而,岁月无情,物是人非,往昔能否失而复得?旧情能否死而复燃?
这篇小说具有茨威格小说的典型特点。首先是不用人名,小说中以“他”和“她”,来代替男女主人公的姓名。虽然不知男主人公姓什么,但他总算还有“路德维希”这个名字,女主人公始终只是一个“她”,而枢密顾问只落得一个姓氏的缩写“G”。作者本来要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共有的命运,姓名便可有可无。正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没有姓名,男主人公,那位作家,也只有一个姓氏的缩写“R”。《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叫B博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女主人公只是C太太。
促使作者命笔的,并不仅仅是主人公的这段往日的恋情,而是现实对人们命运的粗暴干涉。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多少人间悲剧!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好莱坞的电影《魂断蓝桥》,都是表现战争无情,往事不堪回首,夙愿难以得偿。可叹的是,新的疯狂又在滋生蔓延,战争的温床并未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但是军国主义阴魂不散,许多准军事化的活动预示了这一点。上世纪二十年代法西斯运动甚嚣尘上。一九二一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得政权;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暴乱。小说描写的海德堡的游行队伍,预示着战争狂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会让法西斯上台,也会让新的战争爆发。小说完成于一九二九年,离希特勒上台还有四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十年。看到这些群众场面,不得不佩服茨威格的政治敏感和远见卓识。茨威格一直被误认为是不问政治的作家,只善于描写风花雪月,无视民众疾苦。这篇小说证明茨威格果然是描写恋情的高手,但并未脱离实际。他把这对恋人的恋情描写得缠绵悱恻,细致委婉,入木三分。可是就在这追寻往昔恋情之际,竟插入对现实的描写,触目惊心,振聋发聩。这是茨威格在法西斯上台前便发出的警告,可惜并未为世人所注意。
小说具有茨威格小说的一贯风格,仍然以心理描写为主。这里有一段特殊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从对富人的抵触反感,到对夫人的亲近依恋,最后完全钟情于她。两个孤寂的灵魂,两个渴求恋情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遇。夫人的好心善意,消除了他对富人的反感和敌意,使他对这陌生的房子产生眷恋之情。女主人公并不掩饰她对男主人公的爱。从母姓的温柔关怀,爱护体贴,进而成为动人的柔情。他们的互相接近,互相吸引,互相苛求,竟是真挚的恋情的表现,这一恋爱的过程写得细腻动人,含蓄凝练。作者没有写出她和枢密顾问之间的婚姻有什么裂痕,也不着意描写夫人何时萌生爱情。在意乱情迷的紧要关头,她能显示出惊人的自制力,阻止两人亲密的结合。而男主人公出于对她的敬重和深爱,也能控制住自己炙热的欲火。激情四射,却又诗意浓郁。而男主人公在大洋彼岸为相思和渴望所苦,受到度日如年的煎熬。从思念到绝望的过程也写得令人信服。爱情似乎经受了离别的考验,又终于失败。然而,从旧日爱情的灰烬进发出爱情的火花,说明旧情未泯。这一波三折的内心变化,写得荡气回肠,让读者也随之经历他希望、期盼、绝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心路历程,的确是一篇高雅深邃、细腻优美的描写情爱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