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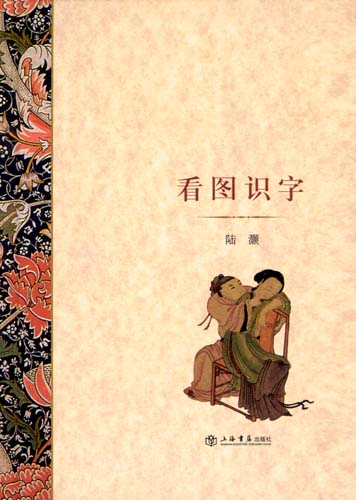 本书共收入随笔文章十五篇,但有些文章的总文题下面还有许多独立的小文章。比如在《真假董其昌》的文题下,另外还有《“君真解人也”》、《题跋中的情事》、《鉴赏轶事》、《真假董其昌》、《名字趣谈》、《不登大雅之诗》,皆以轶事掌故为主,共计七篇短文。在《看图识字》文题下,有《雪夜访普》、《春画》、《一宿因缘》、《马湘兰情书》、《李待问书法有杀气》、《何绍基与赵之谦》、《名联风波的两个版本》、《观无居士周承德》,皆以书画鉴阅为主,共有八篇文章。可能是为了当初在报刊上连载时栏目和版面的需要?书中还写有多位曾经与他有过交往的文化老人的逸事趣闻的长文,如钱钟书、杨绛、施蛰存等。在《默存先生》一文里他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在世风甚浊的年代里,作者内心充溢了一种对品节相高者的仰慕之情依稀可见。 本书共收入随笔文章十五篇,但有些文章的总文题下面还有许多独立的小文章。比如在《真假董其昌》的文题下,另外还有《“君真解人也”》、《题跋中的情事》、《鉴赏轶事》、《真假董其昌》、《名字趣谈》、《不登大雅之诗》,皆以轶事掌故为主,共计七篇短文。在《看图识字》文题下,有《雪夜访普》、《春画》、《一宿因缘》、《马湘兰情书》、《李待问书法有杀气》、《何绍基与赵之谦》、《名联风波的两个版本》、《观无居士周承德》,皆以书画鉴阅为主,共有八篇文章。可能是为了当初在报刊上连载时栏目和版面的需要?书中还写有多位曾经与他有过交往的文化老人的逸事趣闻的长文,如钱钟书、杨绛、施蛰存等。在《默存先生》一文里他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在世风甚浊的年代里,作者内心充溢了一种对品节相高者的仰慕之情依稀可见。
作者读书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阅读规划,多以自我娱悦为主,带有一丝“才子读书”性质的趣尚。所谓有一书,读一书,有一分,乐一分。在闲读中释放身心之累,在品鉴中体悟翰墨之魅。多学淹博,智慧和情趣在文章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浑然无痕。他将读过的书和遇到过的人或事,如果自己感觉有意思的就写出来与读者一起分享。至于读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则并不是他所要关注的事情。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拟,有点类似像金圣叹、袁子才和纪哓岚式等人的风致情怀。有一种从历史故事、野史笔记和人物钩稽中依稀读出当代意义的冲动来。夜深孤灯,独坐静读,与古人前贤文章相伴,虽千百年相隔,文字神交,并不会使人有寂寞之感。
书中有一篇较长的文章《人生边上的事》,比较有趣,但我读了之后也稍有点半信半疑,不可思议:某年(书中是十多年前)他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学术书苑去,刚进书店就被一个中年男子迎面叫住:“我远远看你走来,你的眉心发黑,三个月之内必有大祸。”随后递上名片,上面是佛教什么机构,并说:“我可以为你指点迷津,逢凶化吉。”他当时与绝大多数人一样都不会去理会此类“江湖术士”的,就扔还名片让那人走开:“你走吧,不要吓唬我!”但他回去之后,内心总有些发慌害怕,就去请教研究《易经》的好友指点。好友就拿了一本明人袁黄的《了凡四训》让他不妨一读。这是一本以自己的经历来教导儿子为人处事的书,所以又名《戒子文〉。文章中关于阅读他《了凡四训》的文字,在此不予赘述。他在读了《了凡四训》后,稍有些宽慰。并且有一段时间就少出门,不做“缺德事”,有空用毛笔抄写佛经,此事也就慢慢的淡忘了。
不料数月之后,他去广东出差,先到深圳,再由深圳乘大巴士到广州。他座最后一排中间的座位上,车行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也不感觉到车速之快。突然遇到紧急情况,大巴车一个急刹车,他感觉自己腾空飞出座位,在车内的中间过道上飞过半截车厢,再一路滚翻到驾驶员的脚边……这天差不多就是那个“江湖术士”所“警告”的“三个月之内必有大祸”的截止时间!作者曾经问过黄裳:“你的散文中有没有虚构?”黄先生回答说:“难免。”我如果以后遇到作者,也想私下问他一句:“此事应该没有‘难免’吧?”人生祸福,莫非前定?
在本书中,我比较有兴趣阅读的是那些写曾经与作者有过交往的文化老人的文章,另外还就是关于书画鉴赏品藻方面的文章。书画作品应该无论古今和价格廉昂,亦不可仅看作家的名头大小,关键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艺术水准,以及鉴赏者的审美品位。所以说仅识作者名头大小,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皆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鉴赏家。以我对作者的粗浅了解,他是一个有品味、有天赋并且是量力而为的理性鉴藏者。在书画流通市场或拍卖市场内,在画册和拍卖图录中,在千百幅真赝难辩的作品里,如果你在一二幅或几幅作品前驻足停留,目不转睛,旁若无人。外行绝不会知其所以然,而内行则可知此人深浅。对一个喜欢书画鉴赏的工薪阶层来说,我建议作者不妨侧重于名人手札和旧书(不是古籍)的鉴藏。对古代书画勿轻有非份之念,可用“曾经我眼即我有”的心态视之。
一个作者的文化素养通常可以从阅读和文章两方面来判断。伟大的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3)曾经说过:“一个作者的文章应当是他的心灵的映像,而语言的选择和文字的驾御则他长期操练的结果。”当今不乏聪明和有才华的作家,但很少有人愿意去认认真真地用心读书,他们不愿意追本溯源,不愿意收集资料。而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对阅读充满了乐趣的人,并且他的这种阅读往往超脱了世俗的功利。他的文章会带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我们都不是知识渊博的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需要终身学习和阅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