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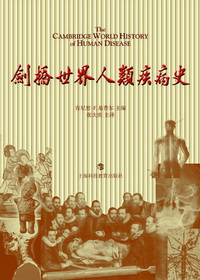 对于处在实用主义劳碌与焦虑中的中国医学界来说,220万字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出版,显得有些“奢侈”。如果要吸引绝大多数临床大夫们的目光,显然是不近世情,仿佛责令激战中的战士离开战壕,去参加一场关于战争史与战争模式研讨的圆桌会议。不过美国学者基普尔为他主编的这部书扩大知晓度和阅读率想出了三条“良策”,一是被纳入剑桥人类历史系列项目,二是名家云集,世界上160位学者受邀撰稿,三是贴近临床,全书2/3的篇幅分科目讨论疾病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演进,是一部连通学术“云端”与临床“土壤”的“顶天立地”的佳作。 对于处在实用主义劳碌与焦虑中的中国医学界来说,220万字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出版,显得有些“奢侈”。如果要吸引绝大多数临床大夫们的目光,显然是不近世情,仿佛责令激战中的战士离开战壕,去参加一场关于战争史与战争模式研讨的圆桌会议。不过美国学者基普尔为他主编的这部书扩大知晓度和阅读率想出了三条“良策”,一是被纳入剑桥人类历史系列项目,二是名家云集,世界上160位学者受邀撰稿,三是贴近临床,全书2/3的篇幅分科目讨论疾病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演进,是一部连通学术“云端”与临床“土壤”的“顶天立地”的佳作。
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抗争史,是人类努力摆脱疾病的自我解放史,也是关于疾病的“认知史”,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共生与适应”的历史。无疑,临床语境中的医生护士感受得更为真切的是“抗争”,是“拯救”,关注得更多的是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学路径与机制。但是,如果跳出现场思维的疾病镜像,转入宏大的历史与地理“宽镜头”,我们就会直面更多共生与适应的命题,人类疾病的“世界地图”展示的是社会、历史、文化与文明的疾病演进路径和机制。
伴随远征、环球旅行和国际贸易的日趋频繁,还有市场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们急切描绘完整的世界疾病图景,建立全球视野的疾病史,这种根植于历史与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的“疾病史”一定不同于病床边的“个体疾病史”,它还不只是扩大了考察和分析的“半径”,而是悄悄挪动了“圆心”,颠覆了传统的疾病认知姿态和解释语码。它将催生历史社会学与医学社会学的结合,为人类历史的灾变规律研究提供观点和资料的佐证,从中洞悉疾病自然史与人类社会生活史之间的强烈互动。
对个体生命而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宿命,但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而言,疾病是改变人类文明方向和进程的“缰绳”,马尔萨斯关于社会灾变、文明衰落的学说就曾聚焦于疾病史,尤其是瘟疫史的研究。诚然,罗马帝国的衰亡(历史上有强大的罗马帝国断送于一群“蚊子”之说,即蚊子传播的恶性疟疾打败罗马军团),玛雅文化的神秘失落,近代美洲大陆土著民族疆域、人口和文化的迅速沦落,都与人类疾病演化的大谱系、大规律相勾连。还有政治领袖的疾病与死亡,即所谓“病夫治国”对历史变局的“偶然性”触发,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命题。可见,人类的疾病自然史是解读人类进步历史的重要“钥匙”,是人类“大历史”画卷中最壮烈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读这部书,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直抵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关节、大关怀。
无疑,当今世界的疾病谱系正经历着由单一病原、大规模轰击、恶性发作的模式向着多因素生态、生活方式影响、大样本散发和内源性基因突变决定论模式转换,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精神或心理不适的各种神经症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不错,人类在过去一百年里创造了奇迹,天花被人类成功地控制了,恶性传染病在大多数地区只是散发,很难形成大流行,但家畜家禽传播源性疾病(疯牛病、禽流感)却恶涛汹涌,艾滋病和SARS在明处或暗处不时地袭扰着人类,难治型结核也试图“东山再起”。尽管现代医学高度发达,但人类社会却危机四伏,灾难不穷,医学的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受到挑战和限制。
值得指出,这样一部坐标式的人类疾病史没有忽视中国,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古今中国的疾病源流和变迁,却忽视了中国大陆的疾病史学者,28位编辑委员与160位撰稿人中没有大陆学者,担纲中国部分写作的是海外的医学史专家(如德国的文树德,英国的华裔学者鲁桂珍),和中国台湾的医学史学者(如梁其姿)。显然不是大陆学者的研究水准有问题,而是我们在跨文化学术交流中的声誉和影响力还有待加强。自然,我们支持医学史研究的目光和掌声也该更“奢侈”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