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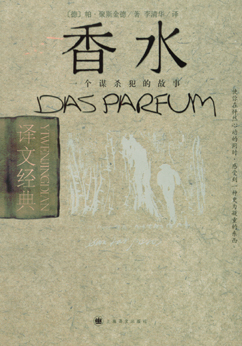 在古代,女人被当作父族的和亲礼物,赠送给潜在的敌对族群。英国人种学家E·B·泰勒说:either marrying out or being killed out.(要么把自己嫁掉,要么给他们杀掉。)乔治·巴塔耶在《色情史》里把女人比做香槟酒,说一个拥有香槟酒的人,如果他小气,不给人喝,人家就要跟他打架,他必须把酒放到一个“交换”的过程当中。结构主义派的人类学家认为这就是婚姻制度和“乱伦禁忌”的逻辑起点:本质上,婚姻是父族之间的相互馈赠。 在古代,女人被当作父族的和亲礼物,赠送给潜在的敌对族群。英国人种学家E·B·泰勒说:either marrying out or being killed out.(要么把自己嫁掉,要么给他们杀掉。)乔治·巴塔耶在《色情史》里把女人比做香槟酒,说一个拥有香槟酒的人,如果他小气,不给人喝,人家就要跟他打架,他必须把酒放到一个“交换”的过程当中。结构主义派的人类学家认为这就是婚姻制度和“乱伦禁忌”的逻辑起点:本质上,婚姻是父族之间的相互馈赠。
《香水》中的父亲里希斯把美丽的女儿视如瑰宝,“在他拥有的财富中,最最珍贵的是他女儿。”他深刻理解这瑰宝的价值,因为他并不十分“愉快”地觉察到,在他心中,对这美丽的造物(他自己的女儿)竟然产生某种“可怕的欲火”。古老的乱伦禁忌不准他越雷池一步,退而求其次,他为女儿制定好全盘计划,要把她嫁给“有地位的人”。格雷诺耶对少女的猎杀对里希斯的计划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尽管他洞察到那其中隐含着某种“神性的”目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者要给“神性”这个词加上一个阳性词缀。他虽然尚未得知格雷诺耶的方法,那些复杂的蒸凝、离心抽吸和更古老的源自古代开罗人的油吸法,却能理解对手的整体目的。这个“整体”的“神性”的目的,指涉着作为“整体”的男性收藏之权:它要把每个女性“最好的”东西抽取出来,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图画将悬挂在男权神殿的大厅正中。
里希斯虽然理解“香水”杀手格雷诺耶,却仍然要抗拒他。那个男性的“理想”跟他无关,里希斯想用女儿交换一些更现实的利益。保护者和捕猎者对那美丽尤物各有需求,这是小说最基本的冲突要素。本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如果上帝想要恺撒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小说结尾安排捕猎者胜出,或者是因为作者的德意志倾向:黑格尔式的“绝对目的”终将获得胜利。但追古溯今,父权的实际利益往往更占上风。现实生活中,祝英台们未必都香消玉殒,而祝员外们,多半都从马文才们那里,兑换到了他们想要的利益。
《香水》并未对里希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欲火”充分展开——乱伦禁忌的确是性伦理最坚硬的内核(由此的确能够看出它必定是婚姻家庭制度的起点),所以哪怕只是提起它,都要小心翼翼。自从弗洛伊德抛出所谓“恋父情结”的概念,坚果便出现裂缝。不过弗洛伊德与其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家,他想单单在心理上找到产生乱伦欲望的依据,最后被证明不成功,但他却为后来的作者找出一株新的母题之树,枝枝杈杈旁逸斜出。不过,饶有趣味的是,那些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颠覆禁忌的作品,大多都避开了真正的父女关系。路易·马勒1992年的电影《毁灭》(Damage)中,不伦之恋在父亲和儿子的恋人之间发生。另一位法国导演贝特杭·布里叶的《漂亮的爸爸》(Beau Pere)里,故事发生在养女和继父之间——这位继父也的确相当英俊,无愧于继父名号(法语“继父”的字面含义就是“漂亮爸爸”——beau pere)。这位漂亮爸爸最终不敌“乱伦禁忌”的强大心理压力,让养女回到生父的身边,尽管电影的尺度放得很开,但结尾仍然安全着陆,回到了伦理的轨道上。
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冲突往往都是在两名男子之间展开,比如《毁灭》中的那对父子,《漂亮爸爸》中的生父和养父,似乎那名作为争夺目标的“女儿”本身倒是无关紧要的。她既可以喜欢情人的父亲,也可以跟养父上床,乱伦禁忌对她并不构成什么心理上的压力。仿佛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伦理禁忌与女性无关,这一点就和女性本身的归属权一样,始终是男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