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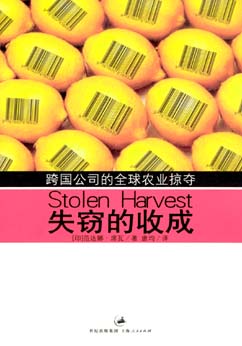 □刘兵兄,还记得我在你办公室电脑上拷贝的一首《喜唰唰》,歌中唱到:“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我忽发奇想,要是这本书作者席瓦能听懂的话,她一定会别有会心——这几句歌词,不正是席瓦想要向对西方跨国公司怒吼的吗?其实席瓦说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那些事,有许多在中国也同样发生着,但似乎未见中国学者发出像席瓦那样明确的质疑和抗议。因此对席瓦的说法,我不敢百分之百相信,她或许也有些偏激之辞。不过,考虑到她指出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往往还没有被人们注意到;考虑到她认为某些对当地非常有害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往往还被认为是大大的好事,这本小书就显得相当有意义了。 □刘兵兄,还记得我在你办公室电脑上拷贝的一首《喜唰唰》,歌中唱到:“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我忽发奇想,要是这本书作者席瓦能听懂的话,她一定会别有会心——这几句歌词,不正是席瓦想要向对西方跨国公司怒吼的吗?其实席瓦说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那些事,有许多在中国也同样发生着,但似乎未见中国学者发出像席瓦那样明确的质疑和抗议。因此对席瓦的说法,我不敢百分之百相信,她或许也有些偏激之辞。不过,考虑到她指出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往往还没有被人们注意到;考虑到她认为某些对当地非常有害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往往还被认为是大大的好事,这本小书就显得相当有意义了。
■如果说到意义,我想,也许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其一,作为一位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这是她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著作,虽然此书并非专门谈论生态女性主义,但实际上在此书中,又确实表现出了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特点,包括对于第三世界所面对的特殊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系的注重。其二,此书是国内不多的深刻地反思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与那些跨国公司的复杂关系,并警示性地提醒人们注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样的发展道路所面临的可能的陷阱与危机。其三,仍是与生态女性主义和有关第三世界问题的立场相联系,对于许多以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促进发展的批判和反思。总体来说,也正像我在其导读中所讲的,这是一部重要的对“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的反思性著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席瓦在其著作中如果说表现出某种偏激的话,我觉得倒很自然,正因为其偏激,而才使其著作有一种特殊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才令人警醒。
□这几天我留意了一下关于印度的报道,看来这样的书出自印度学者笔下,还真不是偶然的。我的感觉是,印度民众对于外国资本的反感,似乎比中国民众要强烈。例如最近印度西孟加拉邦发生农民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导致14名农民死亡,邦政府不得不宣布搁置经济特区计划。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政府的经济特区计划需要征用农民的土地,而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最终酿成流血冲突。在这个事件中,一方是印度的农民,一方是外国的跨国公司,还有一方是印度政府。农民和跨国公司冲突,政府虽然乐意让经济特区计划得以实施,但闹到民怨沸腾的地步,政府也不得不让步。
我联想到第二章中的芥子油问题。印度农民本来主要食用芥子油,小型芥子油作坊和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在席瓦笔下被描绘成一幅不乏田园牧歌色彩的和谐图景。但跨国公司的大豆油打进来了,最终一次神秘的“芥子油掺假”事件让印度政府下令禁止一切芥子油的生产,于是跨国公司大获全胜,印度人民从此改为食用大豆油。这个故事中也是一方为印度农民,一方为跨国公司,还有一方是印度政府。只是在这个故事中,印度农民的反抗没有成功。
■印度农民的反抗是一个方面,不过,反抗是否普遍,以及成功与否,与社会文化和体制关系很大。不过,在这里,我倒更为关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即在这些反抗背后的理论支撑问题。
之前,虽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但至少我们都注意到女性主义理论的进展。而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超越原来主要以西方(以及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立场为主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进展,就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现。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是极有借鉴意义的,它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各种实际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应用问题、医疗问题等等,包括像这本书里所讲的农业问题(其实这也与像转基因这样的高新技术密切相关),都有着特殊的关注和独到的批判性反思。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新理论,在我们这里却传播甚少。这恐怕不能说不算是学术界的一种失职。
□我也注意到国内在这方面的欠缺。书中认为:欧美的富人自己要吃对虾,但人工养殖对虾对环境破坏很大,所以跨国公司就让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来养殖,他们来收购。结果欧美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吃到对虾,而印度的沿海地区环境迅速破坏。类似的故事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复上演,而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时还为可以“出口创汇”而沾沾自喜呢。这种“先脱贫要紧,环境问题以后再说”的心态,在中国也常见。
你说到学术界的失职,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某些专业的研究生,本来是非常热衷于做与现实密切挂钩的“政策研究”课题的,但就是在“政策研究”这个方向上,我们很少看到国内有人做席瓦这种揭露弊端的课题,而那些点缀升平或无关痛痒的所谓“对策研究”则随处可见。这当然也不难理解,现在人们都很“务实”,去做一个得罪跨国公司、批评地方政府的课题,资料又难找,对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也有害无益,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眼下国内谁会愿意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