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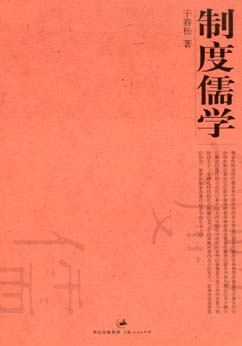 一 一
现代学者一致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政治、社会、教育制度的改变,儒学已经陷入了困境。然而,从20世纪哲学史来看,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代表的现代儒家哲学及台港当代新儒家的哲学,他们的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哲学”在20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相当活跃的。为了分析和说明这两者的分别,我曾提出,“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学(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现代儒家哲学和当代儒家哲学虽然十分活跃,但是这样一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学”以为基础。所以,现代儒家哲学尽管是对于儒学现代困境的一种哲学的回应,甚至在现代哲学论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却仍然不能改变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一文化层面的尴尬处境。
20世纪后半叶,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少。加州大学的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像古玩一样珍爱着。”
这个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列文森并没有说明“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是指什么,我们常见的类似的说法是农业文明或封建社会,意思是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儒学,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今天不仅已失去意义,而且不可能再存在。但是这种说法虽然合于某种历史观,却并不能作为论证。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在古代社会产生的,有的甚至产生在农业文明尚未发展的时代。佛教、基督教都产生在奴隶制时代,但不仅在封建时代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经历发展和转化,直至今天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所以,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或实践体系产生在何种时代和社会,与它是否具有超越该时代和社会的价值意义、存在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正如杜维明针对列文森所指出的,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2]所以,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的普遍性和存在的普遍性。
其次,儒家思想自辛亥革命以后的近百年问,是不是“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而无所作为”?如果就儒家的基本价值、思想方式、行为特性而言,显然并非如此。李泽厚曾指出,孔学在历史中已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思维、情感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事务、关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积淀为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它不完全、不直接依赖于经济的基础或政治的变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具有适应不同历史阶段和阶级内容的功能与作用。[3]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东亚研究中儒家伦理的角色受到了广泛关注,更显示出儒家伦理的价值不仅不是仅存于少数人的心底,而且很明显,在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作用。就哲学而言,冯友兰的新理学在抗战时期,当代新儒家对当代社会文化都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则不是思想的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背景,而是思想得以生存发展的制度条件。余英时在1988年提出“游魂说”,他认为,儒学决不限于历代儒家经典的教义,也包括儒家教义影响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虽然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不见得是儒学的充分表现,传统的儒学和传统的制度不能划等号,但儒学确实往往托身于这些制度,儒学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社会结构之上的。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解体了,儒学与这些制度和结构的联系中断了,于是现代儒学成为了“游魂”。[4]所谓游魂就是在失去制度支持后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论说,作为一种精神,而离开日常生活,这样的儒学在现代仍然可以存在,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了。就儒学与制度化的基本观念而言,本书的制度化问题意识可以说也是沿着“制度一游魂”说这个方向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