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儒家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总结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总书记还曾多次看望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汤一介等儒学研究者,考察位于曲阜的孔子研究院等儒学研究机构,对深入开展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寄予厚望。“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新时代如何书写儒学史,推进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成为哲学人文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作为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由汤一介先生创立)副院长,干春松教授的新作《儒学小史》,正是一部综合前沿学术成果并面向大众普及儒家思想演化历程的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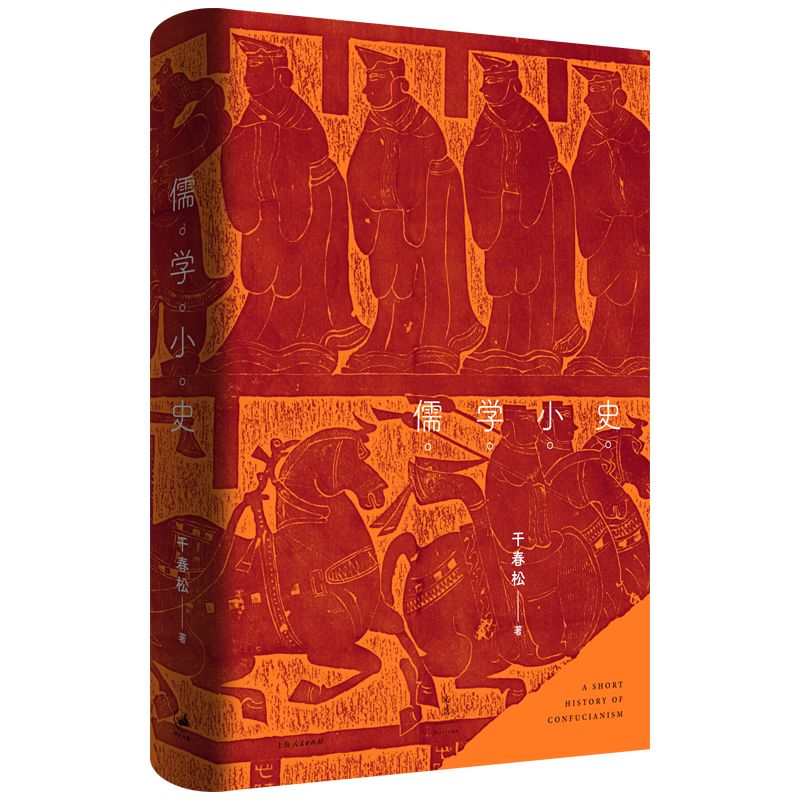
《儒学小史》
干春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丨2019.5
干春松教授师从中国哲学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方克立先生,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5年10月起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等,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论著包括《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学概论》等。《儒学小史》出版后,《光明日报》发表了干春松教授的文章《我是怎么写起儒学史的》,其中阐明了他写作本书的初心,以及从儒学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入思考。
我是怎么写起儒学史的
(一)
200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做老师,最初是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归口哲学系管理。不过,那个研究所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启动,也没有具体的研究项目,所以我便在哲学系“挂单”。
既然到了学校,就要上课、带学生。当时哲学系实际主持工作的张志伟老师建议我在西方哲学教研室带硕士。学生的兴趣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很显然,这内容我指导不了,在西哲教研室的其他老师的帮助下,学生完成了学业。这样,我很“奇异”地有了一个学西哲的学生。不过,这个学生硕士毕业之后,就转而读中国哲学的博士了。
不知什么机缘,第二年我就改在中国哲学教研室带硕士。但我在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身份”一度不甚明朗,《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主干课,主要由比较资深的宋志明、向世陵、彭永捷等教授开。那我应该开什么课呢?这个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并有一些反响,我就问系里,在教学方案中是否有“儒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一查,果然有一门《儒学源流》,原先是杨庆中教授开过。不过庆中兄因为《周易》研究名重天下,专业和选修课的需求很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开了,这样我就接过了这门课。
21世纪初,儒学的“名声”还很成问题,我自己也比较倾向于“中立”“客观”地研究儒学,有朋友称我这种立场是对儒学在近代的衰落“幸灾乐祸”。这么说虽非全无道理,但忽视了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现象,即许多21世纪以来的儒家思想的同情者大多是从“批判”开始的。大概我也属于天生的不安分者,经过一段时间对儒家经典的阅读,我认为以原先的“中国哲学史”(我们最初接触《中国哲学史》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思想传统是“不匹配”的。因此,参与了当时争论激烈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现在的状况来看,葛兆光先生是正好在撰写《中国思想史》,陈少明先生则是在思考将思想家和思想事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而我自己的关切则在儒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关系上。因此,我所设想的《儒学源流》课程,就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也是儒家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