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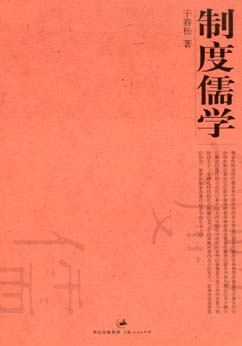 自从200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迁徙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因为一度无所依托,所以享受了几年休闲的时光,同时也得以有精力进一步思考 “儒学和制度”这样一个主题。期间因为主持一个北京地区的“青年儒学论坛”,有机会与许多与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年轻的同仁们反复探讨儒学在现在中国之可能发展的问题,许多次的争辩,激发出许多新的思考,这本书基本上是在这些因缘下的产物。 自从200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迁徙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因为一度无所依托,所以享受了几年休闲的时光,同时也得以有精力进一步思考 “儒学和制度”这样一个主题。期间因为主持一个北京地区的“青年儒学论坛”,有机会与许多与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年轻的同仁们反复探讨儒学在现在中国之可能发展的问题,许多次的争辩,激发出许多新的思考,这本书基本上是在这些因缘下的产物。
自从《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出版之后,得到了一些正面的评价,但是也被我的朋友陈明等人批评为对儒家的现代命运“幸灾乐祸”,其实我也没否认,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儒家的同情和敬意固然重要,但是理性、冷静的分析、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在许多的“儒家实验”主张,在近代以来,都有了先例,而仔细分析这些实验的前因后果以及结局,可以使我们吃一堑,长多智。
我个人十分喜欢黄玉顺的一句话“人天然是儒家”,原因是儒家所讲的都是人之常情。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在一百多年的模仿、借鉴、吸收中,我们忽视了许多我们本身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制度、价值资源,因此我们不免有些茫然,但是20世纪末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中国人重新获得信心。我们开始有可能以肯定的目光看待我们曾经拥有的。当然我们也必须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20世纪中国人所做的一切,因为任何的曲折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经验。
现在,对于儒学的讨论还经常会被上升到非学术的高度,这是儒学本身的观念性和制度性相结合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经常会就“儒学”和“ 儒家”的称呼发生疑惑。这些均是十分复杂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关键是我们无法逃避儒学,这就意味着认真地、创造性地对待儒学就是我们的责任。欣慰的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本书的写作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其中“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一文是与赵剑英合作的,“一个乡绅的心情:刘大鹏日记解读”是与潘宇合作的。还有一些章节的写作要感谢陈来、赵汀阳、邓正来等先生的帮助,尤其要感谢陈来老师拨冗赐序。
同时还要感谢梁涛、方朝晖、彭国翔、彭永捷、陈明、唐文明等这些经常在一起讨论的道友。
本书的出版过程也是许多朋友帮助的产物,感谢韦森、高全喜先生,还有世纪文景的施宏俊和何晓涛先生,他们对于中国学术事业的执着与效率令人感动。
四十不惑,我已经四十岁了,虚度光阴如许,无论如何,我应该感谢生活给予我的一切。感谢已经90岁的祖母在我童年时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感谢潘宇为我所做的无数“琐碎”的事。
写于2005年冬,修正于2006年春 北京万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