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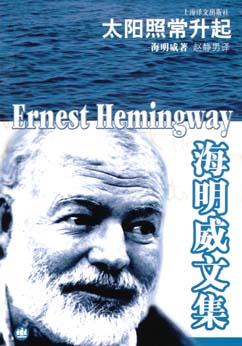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以往很多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围绕以男主人公杰克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或是海明威简洁明快的文风为主题,而女主人公勃莱特则较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评论都是把她归为“魔女”、“妖女”。1952年卡洛斯·贝克将勃莱特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魔女作了比较,称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危险人物”,进而得到结论是“总而言之,她是该进地狱的、让人致命的30岁的女人”,“魔女”一说从此确立。爱德蒙·威尔逊也认为勃莱特是“妖女”、“有彻底的破坏力量”。很多负有盛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也都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勃莱特便成为文学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妖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1996年出版的《剑桥海明威指南》和1991的《勃莱特·阿施利》中多篇论文则指出勃莱特不是什么魔女,而是西方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那么勃莱特究竟是“有彻底的破坏力量的妖女”,还是“西方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海明威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表达了他怎样的妇女观呢?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以往很多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围绕以男主人公杰克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或是海明威简洁明快的文风为主题,而女主人公勃莱特则较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评论都是把她归为“魔女”、“妖女”。1952年卡洛斯·贝克将勃莱特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魔女作了比较,称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危险人物”,进而得到结论是“总而言之,她是该进地狱的、让人致命的30岁的女人”,“魔女”一说从此确立。爱德蒙·威尔逊也认为勃莱特是“妖女”、“有彻底的破坏力量”。很多负有盛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也都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勃莱特便成为文学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妖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1996年出版的《剑桥海明威指南》和1991的《勃莱特·阿施利》中多篇论文则指出勃莱特不是什么魔女,而是西方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那么勃莱特究竟是“有彻底的破坏力量的妖女”,还是“西方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海明威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表达了他怎样的妇女观呢?
《太阳照常升起》集中反映了战后一代青年的思想和道德危机,表达了他们内心的苦闷与迷惘。我们要想真实准确地了解勃莱特的形象,就必须了解当时美国一战后的文化背景。首先是西方战后的精神危机,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摧毁了人们的家园,而且也无情地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念。随着传统观念价值体系的崩溃,一战后的年轻人陷入了精神的荒原中,他们打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泯灭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出路。再加上一战后,美国从战争中发了财,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经济蓬勃发展,美国社会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政府提倡享受、鼓励“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宣传张扬个性,这些新的生活理念使众多年轻人滋长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享乐、放纵自我的思想。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股纵情寻欢的情绪,精神世界的荒芜与物质享受的联合扼杀了战后一代年轻人,他们逃避责任,没有理想,想要在寻欢作乐中解脱精神上的痛苦,那样只能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其次是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战后,美国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和冲击引起妇女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尤其是在一战中,大批男子走上了前线,很多工作的空缺都是由女性顶替的,妇女在经济地位上的独立,势必使妇女也想提高在政治上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英国议会于1918年、美国国会于1920年分别通过了法案,使英美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满足于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要求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她们渴望和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她们模仿男人,穿男人的衣服、吸烟、喝酒、闯入男人的活动领域,以期做到与男性一样。正如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所描述的:“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或者干脆不穿紧身衣,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时并不感到拘束,她们一边从结交恋人谈到节育,一边在午餐的两道菜之间吸烟。”
由于妇女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以及战后旧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分崩离析,男性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开始瓦解,父权文化逐渐衰落,男性权利在一战前后正经历变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化迫使男性努力去重新调整他们的男性身份意识,处在那个时代男性的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应加强自身的男子汉气概,以保持男性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及对抗女性所造成的男性地位丧失。
第三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当时已经趋于崩溃的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战后,弗洛伊德主义在美国广泛得到传播,尤其是“性压抑”的理论不仅被大大强化而且被曲解。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人们的正常性欲遭到压抑的话,那么人的生理与精神都会遭到疾病的折磨,造成人格的失调。反之,性欲或性的活力的自由表现则有益于精神健康。美国年轻人叫嚣着要打破一切传统的道德约束,认为每个人都有满足自己性欲的权利,满足自己天生的性欲是不应该受到任何道德约束的。于是美国当时的年轻人把它当成“性解放”的理论支柱,他们为自己的放纵找到了借口,“以前受到谴责的出格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得到了理性化的甚至是浪漫化的解释,而施于谴责的人反而变成了压抑人性的变态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