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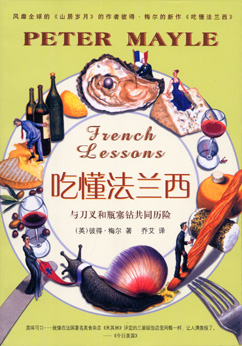 French Lessons直译为“法语课”。第一联想,是法国小说家都德(Daudet)的《最后一课》。小说里的那堂法语课之所以惊心动魄地好看,在于其无处不在的张力,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个“禁止法语课”的巨大的阴影。大家都知道,这个阴影,这个敌人,指的是“只许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教德语”的普鲁士当局,“那些坏家伙”。 French Lessons直译为“法语课”。第一联想,是法国小说家都德(Daudet)的《最后一课》。小说里的那堂法语课之所以惊心动魄地好看,在于其无处不在的张力,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个“禁止法语课”的巨大的阴影。大家都知道,这个阴影,这个敌人,指的是“只许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教德语”的普鲁士当局,“那些坏家伙”。
拔剑四顾茫然的侠客说:“无敌最是寂寞”。“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这是小说家言。最起码,在叙事的技术层面,上法语课和吃喝活动一样,必须设置一个敌人,方能将口腔活动激活至空前活跃并刻骨铭心之境地。我们看到,一旦有旁的儿童在一起争抢,平时不肯好好吃饭的儿童通常都会因这些“普鲁士当局”的出现而突然变得胃口大开,甚至暴饮暴食起来。
梅尔先生深谙此道。在“普罗旺斯系列”中,那个英国人代表着我们大多数人营营役役的生活状态,与普罗旺斯懒洋洋的阳光之下的那种“神仙过的日子”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全身松软地、幸福地败下阵来,煞是好看。在大众的想象里,英国人,英国成年男人,本来就是“拘谨”或“沉闷”的代名词。这还不算,梅尔先生不仅是英国人,而且几乎就是地球上郁闷生活的杰出代表。上阵之前,他在麦迪逊大道上服了十五年的“苦役”,狼奔犬突,惨不忍睹。饮食问题上,英国和美国更是出了名的乏“膳”可陈,尤其是前者,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只求一饱,不死就可”的英国人杀猪是杀两次的:第一次是杀猪,第二次杀的是猪肉做成的菜(当然,炸鱼薯条、猪肉馅饼、羊肉薄荷果酱以及什么牛肾烘饼之类的“淡出鸟来”,今天已逐渐淡出伦敦之时髦饮食圈。伦敦和纽约、巴黎一样,皆以fusion为最in旗帜--为之鼓与呼的彼得·梅尔似乎功不可没)。
至于英国人对待吃喝的态度,在我们的“想象共同体”当中,更一向被视为全人类之“美食公敌”。我们一直相信,或者将信将疑地相信,对待食色,英国人或多或少都怀有某种来历不明的原罪感。据英国饮食杂志GoodFood称:“随着近年英国人开始慢慢的讲究美味,以往给外界留下的那种刻板印象正在逐渐被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是:“过去的英国人曾经是最不讲究吃的民族,他们认为食物不过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材料而已。”这一次,彼得.梅尔为我们制造的这个“有趣的坏蛋”以及“开胃的敌人”,依然是过去的那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垂涎三尺,在由“刀叉和瓶塞”组成之法兰西阵中进行“历险”,老鼠掉进米缸,猪八戒闯进了女儿国,自然是加倍地活色生香,张力十足。当英式的“罪恶感”与法式的“最饿感”陷入混战,百感交集,岂有冷场之理?Adventures with Knife,Forkand Corkscrew,与刀叉和瓶塞钻共同历险--正是这本书的副题。虽然在广大读者的想象中,梅尔于饮食一道早已修成正果,但是他似乎是越活越“回去”了--至少在这本书里,他老人家一上来便以一个“童贞丧失者”的形象出场:“第一口咬在法国面包和法国黄油上,我那还在沉睡中的味蕾突然苏醒了,一阵痉挛……我失去了我的童贞,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饱食终日,常怀赤子之心”。听这个怀着“饮食原罪感”的英国人将其“丧失童贞”之全过程娓娓道来……“一阵痉挛”紧接着“一阵痉挛”,这回真的搞大了。
我唯一替梅尔和他的出版商感到担心的是,大部份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未必能随着梅尔的“痉挛”而“痉挛”。并不是要怪罪谁,要怪,就怪中国菜大大的好吃,因而“痉挛”不起来。一般相信,法式精馔技艺正是得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533年,意大利佛罗伦斯的凯萨琳公主嫁给法国国王,做为陪嫁,30名佛罗伦萨大厨浩浩荡荡开进凡尔赛宫。从此君王不早朝,因为从此以后,凡尔赛宫的奢华晚宴每每是通宵达旦--而埃兹拉·庞德在《比萨诗章》里偏偏这样写道:“全部的意大利,也比不上一道中国菜。”此外,像梅尔在本书中提到的足以令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致大痉其挛的“又鲜滑又爽脆,浓郁的蒜香里还清晰地散发着香芹的味道”的田鸡腿以及“成为大蒜的载体”的蛇,诸如此类,在中国的好吃之徒们看来,不过家常便饭。至于作者津津乐道的那种因为被法国人以“人道方式”喂养而吃起来美味不可方物的“布雷斯鸡”,在汉语里无非就是比“农场鸡”好吃的“放养鸡”。区别只是在于,杭州话叫“本鸡”,广东人叫它“走地鸡”--尽管如此,《吃懂法兰西》中文简体字版的问世,相信不致于造成“过屠门而大嚼”或者“把冰卖给艾斯基摩人”这样不幸的局面,就算你是一个属于那种一到外国就急着到处寻找中国餐馆的中餐死硬份子,即使French Lessons这样的用语对你这样的饱学之士显得有点不敬,也不妨将此书当做游记来读。事实上,当年《山居岁月》正是以“年度最佳旅游书”获得了英国书卷奖(English Book Awards)。泰晤士报当时说它“是一出高级喜剧”,并且“机锋百出”、“让人爱不释手”。不管你好不好吃,亦无论爱不爱玩,我相信泰晤士报的上述评语对本书及其各国读者依然有效。如果不足以重温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之丧失,何不把这一遭的阅读体验想象成一次足不出户的艳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