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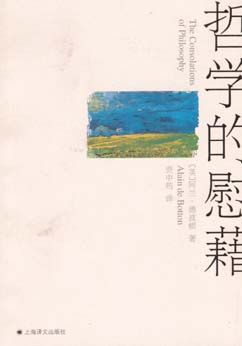 长久以来,对于作家的才华的衡量,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因为文无定法,也因为作家们太过于强调自己的个性,以至于不可能形成一个行业规则。百花齐放的同时,一百只乌鸦也在自得其乐地聒噪。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他的畅销随笔集《哲学的慰藉》中说:“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套用一下,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广而言之,以那位希腊诗人(荷马)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求得生活的认识。” 长久以来,对于作家的才华的衡量,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因为文无定法,也因为作家们太过于强调自己的个性,以至于不可能形成一个行业规则。百花齐放的同时,一百只乌鸦也在自得其乐地聒噪。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他的畅销随笔集《哲学的慰藉》中说:“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套用一下,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广而言之,以那位希腊诗人(荷马)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呼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求得生活的认识。”
这里所谓认识的对象,既可以包罗自然万物,又可以涵盖人心民情。曾几何时,作家们的最高目标在于再现人与事物的细节。蒙田认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可以为扫帚立传,巴尔扎克为了一张桌子可以耗费十页笔墨,而普鲁斯特浩浩荡荡的《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不过是描述一块小cookie——如今,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为饼干,二为浏览网络时所接受到的反馈信息。生活大致如此,一则我们在生活,二则我们生活在满山遍野的他人对我们的生活的反馈(肯定或否定或模棱两可)之中。文学的野心,则是竭力描述二者的合集。而对一个作家才华的衡量,则要依赖于他的描述能力,而非意识形态上的与时俱进与否。阿兰·德波顿的爱情小说《亲吻与诉说》展现了一个人如何描述另一个人的过程——古往今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大多不脱离主角A回忆主角B的模式,这也是一种描述;阿兰·德波顿的才华所在,则是他的主人公并没有落入哀伤回忆的窠臼,而是基于对“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的“同情”,决心描述自己的下一位恋人,为她写一本传记。
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叙述者“我”曾经有过一位同居六个月的恋人,二人分手,“我”惨被指责为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从不关心任何别的东西。在一家书店,我看到一本维特根斯坦传记上的广告词:“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富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我”忽然认识到理解别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趣的过程,于是在与下一位恋人伊莎贝尔约会的过程中,开始写作伊莎贝尔的传记,窥视、揣测、分析她的生活与隐私,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描述恋人伊莎贝尔的已有的一生。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恋人,足够恐怖,而在这本小说中,则是妙趣横生——这种妙趣,也是英国式的,冷而幽默,同情中含有讥笑,尖酸中潜藏智慧。
这部怪异的小说,在开篇就提到了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读者——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为何物的人不必往下读了!因为这本书不是一本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而是一本“唠唠叨叨”的“说理”小说。即使两人躺在床上,女主人公伊莎贝尔讲述自己“惊心动魄”的性经历的时候,“我”依旧能够展开有理有据的思考:“叙述肉体的欲望总有一种力量,它能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一个故事一旦开始,我们就会回复到普通的洞穴人的生活状况中,围着篝火啃猛犸象肋骨,渴望能找到那个被有教养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十分庸俗的问题——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的答案。”——作者在这里顺手一枪刺向了“有教养的文学批评家”,这是基于英国传统。在中国,作家此刻只会中途变招,感激涕零地由刺转拍。
天可怜见,这部小说不仅由男主人公看到“维特根斯坦”而起兴,却又让女主人公在书的中间阶段撒谎自己读过“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是美国哲学家和小说家,女,江湖传言,她不仅貌美如花,而且思想深刻,并且是一个双性恋者,属于维特根斯坦的对立面——二人的作品也成对立,维特根斯坦的书几乎没有人会去读或者能够读懂,苏珊·桑塔格的书却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莎贝尔撒谎,而在于她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并且目她为老太婆。小说在此刻由形而上急剧坠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描述了伊莎贝尔挖鼻孔的细节以及见解:“最好的鼻涕是干而成块的,最坏的鼻涕是感冒的时候又湿又散。”苏珊·桑塔格与鼻涕之间的落差,不亚于天国与地狱、哲人与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