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次谢朋友馈赠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之一马波男爵回忆录:“我从未见过那本马波译本,书棒极了。那年月人们的信写得多好,看我们的信写得多糟。”他一生都在谦恭地给朋友们道歉,说自己的信写得“无聊而且愚蠢”,然而,除了很个别的例子,他说的与事实不符。因为,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随处可见风言风语、掌故轶事。有的煞有介事,有的道听途说,庄谐并存,有的是吹牛大话,有的是自我攻击。有抱怨,有忏悔,有给别人的指导,有自我反思,有无边而不乏智慧的捏造,有对朋友和敌人进行的人物素描,有惹人注目的中伤、回忆与预测,也有口无遮拦的文学、政治与社会言论;有某曰某时所做所想的什么,并且连当时的气候信息都有,总之,还有千百个话题,那充满了他活跃丰富的头脑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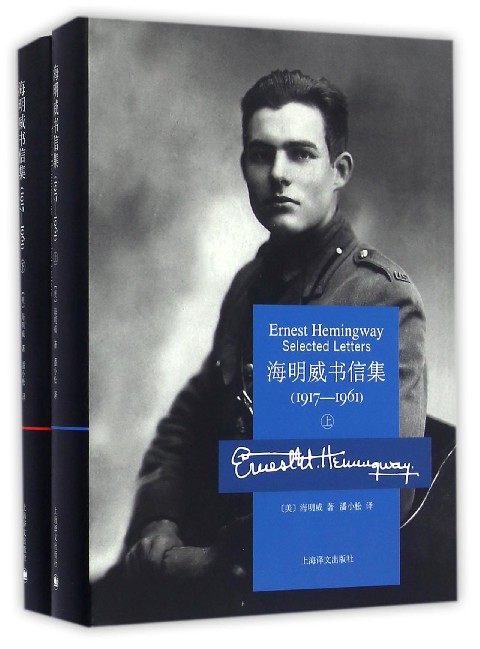
除非场合要求语言细致精准,他的信从不摆出正式的架势,连装都不装。他清楚这一点,心不由衷地哀叹过,其实又满不在乎。“很多时候,写作最好的人往往写信最糟。”1929年他说,“这几乎是定律,”1957年他又道:“此信潦草,满是错字,写得匆忙,是信,不想当散文来写。”尽管老这么说,他自己一定知道日后读者自己会发现,从他的书桌台子抑或打字机书写板上流出的每一封信几乎都给人留下印象: 这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东西,毫无疑问。
成年后终其一生,海明威习惯写信,甚至有写信强迫症。对他来讲,通信是生活必需品,如果算上水火之灾殃及的书信,或者蠹鱼乃至热带虫子咬噬掉的书信,更或者有意无意不声不响扔掉的信(自己或别人干的且不论),再或者箱子里保险柜里堆着的以及被人扣着不见天日的信,在1961年他死之前的50年里,他大约写了六七千封信,还不包括有时长信之后发的洪水般多的电报之类。
假如他没写那么多信,严肃的小说作品也许还要多产些。海明威自己常这么想:“任何时候我能写一封好信,那就是我没在工作的征兆。”他曾经如是说。写信“是摆脱工作的令人陶醉的方式。同时又感觉你干了点什么”。他热爱写信,愿意“浪费”笔墨时间,无论身在何处,朋友在哪儿,皆令妙笔湍流或者涓涓细流。“只有习惯写了才难停下。即便是写信的方式我也愿意跟你谈,尽管话蠢得可悲,并且自说白话。”1951年他对查尔斯·斯科瑞布纳如是说,时正当他书信之花盛开的岁月,约从1949年始,延续至1952年。类似的时期还包括: 比如1924到]928年,他迅速成名的时候,名誉的阶梯有时他爬得快得有点不留情面。再比如1939到1941年,他写《丧钟为谁而鸣》时期以及之后。
即便是写小说顺利的时候,他似乎也需要通过写信来松弛一下创作的注意力。在信里,他笔头松懈,鬼才在乎,长得没谱,措辞重复;而正经写作时却一次超不过500个单词,约束自己给最佳的词汇以最佳的秩序。所以,一天“严肃”界限的写作开始之前,一大早他通过写信来热身,让脑子动起来,手头的故事或章节在下午或晚上放到一边之后,他用写信来“冷却’头脑,很像运动员在赛后于跑道上再慢跑一下。
表皮下是他特有的工作与游戏之间的区分。游戏属于调剂: 在最紧张的工作间歇提供放松,如此严肃的写作才有可能完成。写信是他的一种游戏形式,正因为是游戏,他的信才浑然天成,假如内容和组织都有花费心思之苦,就缺少直截了当了。而写小说则是最艰难的那种工作,为了流芳百世,编故事的人得设计安排。尽管海明威不吝惜时间写信,书信于他还是副产品,是游戏产品,属于一时的创作冲动。书信不是旨在长远的写作,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次跟他说,一个人“写信要总想着身后”。海明威1950年说,这话“给我的印象如此之坏,以致我烧了房里所有的信,包括马多克斯的信。你把只有0.5卡的豆壳攒着等身后?这破玩意儿?那就留着吧。它们可不是为身后写的,豆壳也不是为身后当燃料的,只为此曰此时,身后的事情会自己照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