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离北上广”,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事实而进入公众视线,它也同时成为一种大城市人沉重生活负担的同义词。人们要逃离的其实并非某个具体的束缚,而是北上广这三个超大城市代表的不言而喻的大都会生活方式。
当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共同呼吸着陌生而熟悉的尾气,穿梭在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时,我们很难分辨,大城市究竟让我们自由,还是使我们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中,这样的城市,真的和我们想象的美好生活有交集吗?我们不禁会想,我们的大城市出了什么问题?
2016年8月22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将指导未来24年的上海城市总体发展。草案规划中的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将上海2040年人口调控目标设为2500万(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的上海常住人口已超2400万);二是要求上海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
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限制土地的供应”而控制城市规模的发展逻辑,上海不是个例,而是全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形成的一个定势。这种政策上的努力方向,希望将城市化引向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治理的压力,实际上暗合了时下将拥堵、污染和不安全等“城市病”简单归因于人口增长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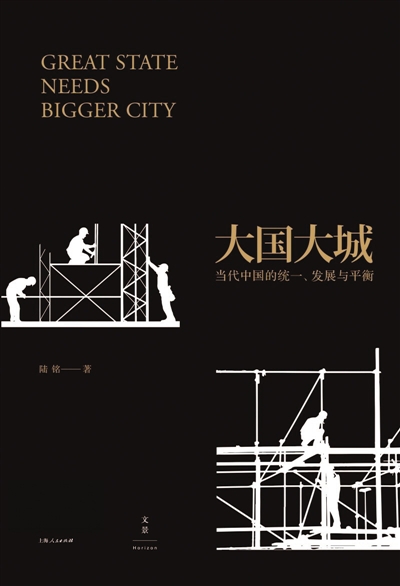
经济学者陆铭在他的《大国大城》一书中认为,上海这样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是由全国总人口规模决定的,而不能单看一个孤立的数字。实际上,在人口和土地需求高的城市,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土地供应,同世界上城市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一致的。
但中国的问题是,“人的流动不自由,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受制于现有的制度和政策,配置也不合理”,因而统一市场没建起来。结果是,适合发展“聚集经济”的上海等东部城市,劳动力短缺,土地供应不足,地价上涨,房价飞涨。中西部地区,土地却供应过剩,工业园荒废,乃至变成“鬼城”。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样的局面隐含着一个比时下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深刻的“欧洲化”问题。如何避免或脱离这样的“欧洲化”?陆铭在《大国大城》中阐释的理念,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脉络。
土地配置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土地越稀缺
新京报:你在《大国大城》这本书中谈到,我们目前的统一市场建立在“土地配置”方面受到了制度限制,简单说来涉及哪些?
陆铭:我们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制度,但把大量指标给了中西部地区,在东部相反,还在严控甚至减少(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适合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地方,土地本该增加供给。但现在,限制土地供应,地价上涨,房价也上涨,这是东部普遍的问题。相反,在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工业园投资过剩。这是第一重限制。第二重限制,这些建设用地,多少建工业园,多少造住宅或商业用地,是政府决定的。普遍情况是,相对于商业和住房用地,地方政府更愿意提供工业用地。第三重限制,商业和住宅,政府宁愿多供应商业,而不多供应住宅——上海的市中心甚至出现商业地产过剩,住房不足。
新京报:土地是市场经济三大要素中最特殊的,不可流动,但土地的使用权却可流动和交易。你认为,即使是存在这些土地配置限制,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陆铭:是的,假如内地省份有建设用地指标,但造的工业园没企业进来,相反,东部某一个城市地价高,但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指标就可解决:内地省份减少一平方公里而东部城市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同时向前者付钱。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没变,土地需求多的得到更多的供应,而没需求的,减少土地供应。
除了政府掌握的建设用地,还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数量减少,建设用地就会出现部分闲置。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交易,以宅基地为例,一个不打算回老家的农民工,就可用宅基地的使用面积,去相应增加他所居住城市的建设用地,同时宅基地复耕,全国总的农业用地也没减少。他在工作的地方,地价远超过他的宅基地在老家的价值,这一部分差价可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来源。
人口流动
“城市病”与人口增长关系不大
新京报:谈到农民工进城,实际上进入到了统一市场的另一个方面,即“劳动力流动”问题。现在还存在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拥堵、不安全和污染等“城市病”,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等所谓的“低端工作者”)造成的,因此要限制他们流动进城,你怎样评价?
陆铭:首先,在世界人类发展历史上,没证据可证明“城市病”的产生是人口多带来的。伦敦、东京和纽约,城市病最严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此后,人口成倍增长,城市病却缓解了。退一步讲,如果真要说人口多导致了拥堵和污染,那么,年收入百万和五万的两个人,相比较而言,谁更增加拥堵和污染?五万的人没有车,甚至不坐出租车,带不来污染和拥堵。像北京和上海,通过驱赶小餐馆和理发店控制人口,可他们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