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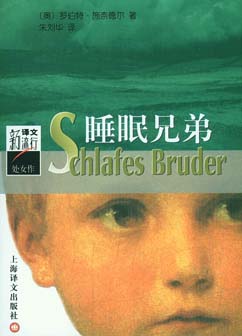 这里,故事发生的地点早已无踪迹可寻,故事的真实性也就更无从考证了,但是故事的真与假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是读小说,就是想逃避真实世界里的种种无奈 ;而书中的世界即使再恐怖与邪恶,毕竟离现实还太遥远,合上小说,也只是为书中主人公掬一捧同情之泪,而不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这或许正是施奈德尔小说所要追求的效果。更何况,没有了任何框架的限制,作家创作起来就更加游刃有余了:除了作者和读者最关注的天才音乐家埃利亚斯的音乐和爱情经历之外,我们不难读出其他似是无足轻重,却又能独立成章的人物故事穿插在其中,如助产妇艾伦索宁,巫师齐丽,碳工米歇尔等等。这种跳跃式的叙述虽然给阅读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施奈德尔张弛有方,既能放,也能收,无数的小插曲仿佛涓涓溪流,终又汇聚在埃利亚斯这条主干河流中。 这里,故事发生的地点早已无踪迹可寻,故事的真实性也就更无从考证了,但是故事的真与假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是读小说,就是想逃避真实世界里的种种无奈 ;而书中的世界即使再恐怖与邪恶,毕竟离现实还太遥远,合上小说,也只是为书中主人公掬一捧同情之泪,而不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这或许正是施奈德尔小说所要追求的效果。更何况,没有了任何框架的限制,作家创作起来就更加游刃有余了:除了作者和读者最关注的天才音乐家埃利亚斯的音乐和爱情经历之外,我们不难读出其他似是无足轻重,却又能独立成章的人物故事穿插在其中,如助产妇艾伦索宁,巫师齐丽,碳工米歇尔等等。这种跳跃式的叙述虽然给阅读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施奈德尔张弛有方,既能放,也能收,无数的小插曲仿佛涓涓溪流,终又汇聚在埃利亚斯这条主干河流中。
主人公埃利亚斯是赛夫的老婆和神甫的私生子,他生性痴迷音乐,并对其有种天生的领悟力:赞美诗使他有了人生第一次呼吸,洗礼仪式上的管风琴琴声令他欢呼不已,就连飘落的雪花也会让他欣喜若狂。五岁那年,他在自己最喜爱的地方--那块被水抛光的磐石上面遭遇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中的顿悟经历。自那以后,不仅他的听觉成百倍地增长,而且他还能恰到好处地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物对话或者模仿陌生人的声音。这次的听觉奇迹为他今后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愚笨的艾希贝格人都显得太离谱,太不可思议。还在受洗礼之前,埃利亚斯那不同寻常的声音就令其养父浑身不舒服,而在听觉奇迹之后,埃利亚斯更因为听觉奇迹的后遗症--黄色眼珠和性早熟成了全村一个无法揭晓的谜。他的父母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将他像“癫痫病人”一样囚禁在小屋里,既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也没有一丝温柔的举动。试想,家人尚且这样冷若冰霜,村里人就更有理由冷嘲热讽了。虽然,艾希贝格人个个身有残疾,病痛缠身,他们却无端地嘲笑他人的不同,并辱骂埃利亚斯是个“眼睛黄得像牛瘟的魔鬼”。
埃利亚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虽然他也曾试图从亲人那里得到抚爱,从其他人那里赢得理解,但命中注定与众不同的他屡被拒之门外,最后连他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他变得越来越孤独、落寞、少言寡语,就在这寂寥之中,他以为在彼得处找到了一份友谊,因为在他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彼得没有抛弃他。患难之交见真情,埃利亚斯对彼得的爱是无条件的,天真的,乃至于是盲目的,即使他并不赞同彼得的举动,他也从来没有想要真正地批评彼得,因为他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朋友;但生性冷酷、曾经纵火想烧死父亲以报断臂之仇的彼得却有自己的想法:他预感到了埃利亚斯的伟大才能,并想控制埃利亚斯。他无疑也爱埃利亚斯,但却是极端自私的,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同性恋色彩。文中将埃利亚斯和彼得的关系喻为水和火的斗争,水火虽不相容,但却互为依存,相伴自始自终。
12岁是埃利亚斯的另一重要人生阶段。这年的基督降临节上,埃利亚斯成了艾希贝格的五个音栓的管风琴的风箱脚踏手,他就此得以研究管风琴构造,纠正其不谐和音,并无师自通地开始演奏他生命中的第一个音。也是这年的圣诞节,他从大火中救出了堂妹伊尔斯贝特,并意识到自己5岁时所听到的心跳声就是伊尔斯贝特的心跳,从此深深地爱上了她。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伊尔斯贝特的爱情当中,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发挥到极限,因为“他是在为伊尔斯贝特演奏,创作音乐,捕捉住她的枯黄色的头发的芳香、小嘴的颤动、她女孩的清脆笑声或兰色缎子裙的褶皱”。
1820年的复活节,埃利亚斯生平第一次在全村人面前展示其音乐才华。他的出神入化的演奏使性情愚钝的艾希贝格人也有好一阵变得像绵羊一样虔诚。1825年,在费尔德贝格管风琴节上的即兴演奏构成了他音乐人生的顶峰: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奏中,他将赞美诗《来吧,噢死亡,你这睡眠的兄弟》 演绎得淋漓尽致,震动了听众内心的最深处,人们仿佛被催了眠,“他们的呼吸放慢了速度,他们的心跳频率成了他的心跳的频率”。
但音乐的辉煌成就并不能完全改变他的社会地位:开始时人们还对他刮目相看,但时间一长,嫉妒与诽谤又慢慢在空气中蔓延开来。而他和伊尔斯贝特的幸福日子也不长久。虽然他一心一意地爱着伊尔斯贝特,但他从未对其吐露过心声,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白;而伊尔斯贝特对他则是尊敬多于爱慕。他的音乐未能为他争取到伊尔斯贝特,因为她并不理解埃利亚斯是在为她演奏,于是,当她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时候,她选择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艾希贝格人做丈夫。
音乐家本就生性敏感、脆弱,当埃利亚斯看到他所追逐的爱情最终只不过是一个空想之后,他彻底绝望了。生活没有了希望,精神没有了寄托,生命也就成了一种多余。而最后一次那过于轩昂、过于磅礴的演奏似乎也耗尽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激情,他的生命无法再延续,他为自己选择了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折磨人的死亡方式--不再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