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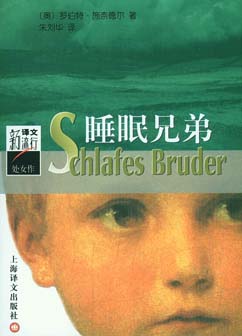 一 《睡眠兄弟》是罗伯特·施奈德尔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1992年,该作品一经问世即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作品之一,施奈德尔也随之被誉为德语文坛上的“神童”。 一 《睡眠兄弟》是罗伯特·施奈德尔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1992年,该作品一经问世即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作品之一,施奈德尔也随之被誉为德语文坛上的“神童”。
施奈德尔于1961年出生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和其他三个孤儿在莱茵河谷阿尔卑斯山区的一户农家里长大成人。他的作品的变幻莫测或许和他的身世有着直接渊源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挺有魔力的”。他不喜欢自己生长的闭塞的环境,对此也从未有过归属感。1981年,他终于能够在中学毕业后离开那小地方,到维也纳开始学习作曲、艺术史和戏剧学,但是学业未成,他突然立志改行当作家了,究其原因也令人不可思议:在一次从萨尔茨堡到福拉尔贝格的火车旅行中,他对自己正在阅读的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作家感到嫉妒万分,“好吧,现在让我做给你们大家看看!”
罗伯特·施奈德尔在所有采访中表现出的自信与狂妄让大众觉得他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人们渴求谜底,希望从他的作品中寻得答案,更何况媒体对《睡眠兄弟》出版经过的大力渲染更加鼓动了人们的好奇心:《睡眠兄弟》1990年就已成稿,但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它被德国各大出版社拒之门外,直到1992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第24家出版社--原东德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对此书表示出一定的兴趣,愿意以谨小慎微的4000册做一次尝试。当时,雷克拉姆出版社频临倒闭,这一决定仿佛是无奈中的一次绝望挣扎。
没想到《睡眠兄弟》出版以后,4000册书一售而空,罗伯特·施奈德尔也因此一举成名。至当年底,该书的发行达到40000册,跃居德国畅销书榜首。一时间,各报刊杂志、文艺批评界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褒奖有加:“一部典范佳作”,其作品“充满魔力”,“叙述技巧完美无缺”等等。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市和媒体导向之间的微妙关系:《睡眠兄弟》商业的成功引发了媒体,即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这些友好且热忱的评论为其进一步打开了通向读者的大门,无疑更对其商业上的成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截止1998年初,该书的销售量达到140万册。在一片喝彩声中,《睡眠兄弟》为罗伯特·施奈德尔带来了一系列荣誉,还陆续被改编成芭蕾舞剧、电影和歌剧。
但即使在如潮的好评中,人们还是常常可以读到一些反面的批评意见:说施奈德尔的作品不过是在玩弄一些“一眼就能让人拆穿的伎俩”,处于“系列泡沫剧写作的危险边缘”,其叙述手法不过是那一类平淡无奇年轻作家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施奈德尔“莱茵河谷三部曲”的其余两部作品--《空行女》(1998)和《处女们》(2000)问世以后,对《睡眠兄弟》的批评就更加辛辣了。这或许是因为评论界在《睡眠兄弟》之后对施奈德尔寄予了太高的厚望,《空行女》刚和读者见面,就被他们批判得体无完肤,全然没有当初洋溢的热情;《处女们》也没能改变批评家的态度,于是乎,连《睡眠兄弟》也跟着受到责难和奚落了。不过,这其中的微妙关系也很耐人寻味:一方面,《睡眠兄弟》的巨大商业成功似乎使其理所当然地担当起施奈德尔后来作品成功的保人;另一方面,人们不禁提出各种疑问:《睡眠兄弟》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创作的新颖和独特,还只是由于它恰逢天时地利,积极迎合了当时大众的口味?其仿古的语言风格是施奈德尔的语言魅力还是拙劣粗糙的一种表现?《睡眠兄弟》曾经让人目瞪口呆,是它的主题震慑人心还只是读者和文学批评一时迷失了方向?更有人直接对施奈德尔的创作能力表现出了怀疑:这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令人惊诧,或者干脆说是运气不错,但第二部作品就完全可以说明他是否具备作家的素质了。
在如此猛烈的批评浪潮面前,施奈德尔却自有高见 :“我的书本不是用头脑来读的,只有用心,你才能理解它”;施奈德尔声称要用自己的激情去为世界创造一个幻境,体验“全新的多愁善感”情绪。那么,《睡眠兄弟》奉献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和怎样一份多愁善感的情绪呢?让我们走进这个世界,来亲自感受这份情感吧!
二
施奈德尔确实很善于构建自己的虚拟世界。小说一开始就平铺直叙地告诉读者“这是音乐家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的故事,在决心不再睡觉之后,他于二十二当龄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将一名叫艾希贝格的偏僻山村里的人情事故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艾希贝格位于福拉尔贝格中部,这里世世代代仅居住着两个既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却又互相乱伦的家族--郎帕特和阿尔德尔,他们既贫穷又固执,既愚昧又狂热,既冷漠无情又忌妒心十足,这一切使得上帝也无法忍受,就在十九世纪连续放了三场大火,把有关它的一切存在烧成了灰烬,然后就轻轻地将它从地球上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