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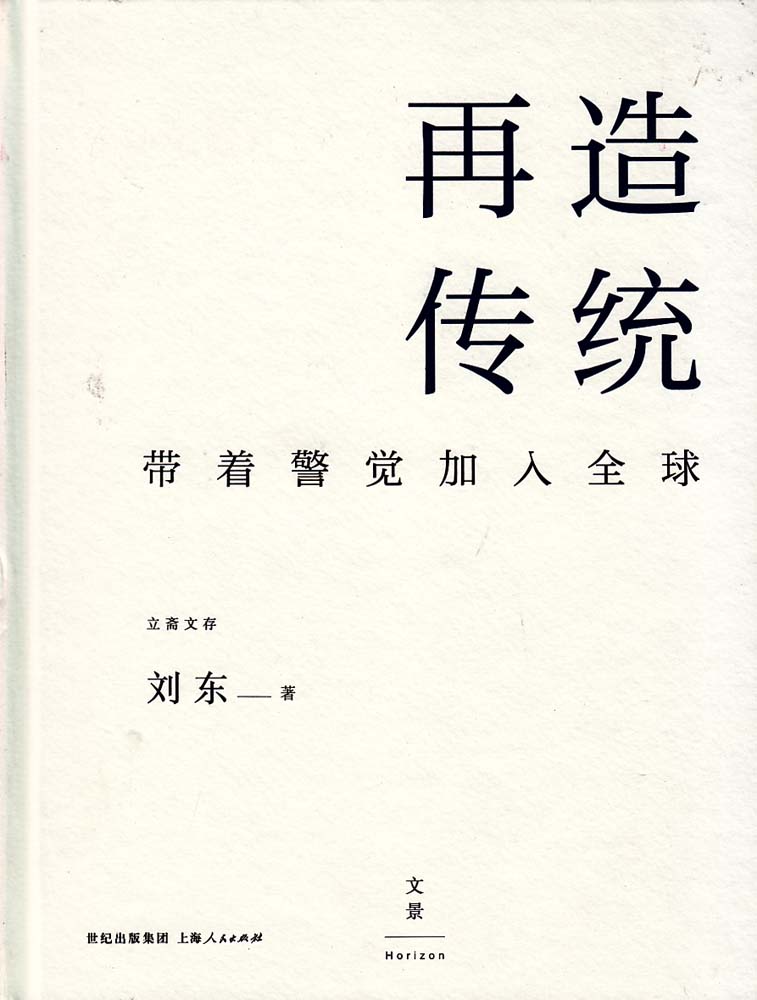 有点奇特的是,这本篇幅原本相当有限的小书,却收纳了尽量广博的内容。——具体说来,自己先是用最前面的两章,来完成对于全球化特别是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描述与理论概括;接着又用位于主体部分的八节,来展示和剖析传统文化在申遗、语言、建筑、电影、熊胆、体育、通识、家庭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最后则以总结性的和分量最重的两章,尖锐地提出了六个层层递进的问题,从而对中国在当今世界所遭遇的态势和承担的命运,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括思考。 有点奇特的是,这本篇幅原本相当有限的小书,却收纳了尽量广博的内容。——具体说来,自己先是用最前面的两章,来完成对于全球化特别是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描述与理论概括;接着又用位于主体部分的八节,来展示和剖析传统文化在申遗、语言、建筑、电影、熊胆、体育、通识、家庭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最后则以总结性的和分量最重的两章,尖锐地提出了六个层层递进的问题,从而对中国在当今世界所遭遇的态势和承担的命运,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括思考。
把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压缩到了一起,难免显得密集和板结。不过,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像我们在研究前人的文字时,总要留意它起初是写在甲骨上的还是竹简上的,或者初衷是写来公布的还是留给自己的一样,任何一种特定的写作风格,都和它的发言语境与书写介质密切相关。——而前文已经开宗明义地交代过,我对这个话题的持续关注,先是从一份应命而作的提纲开始的,后又受到一次教学任务的激发,因此,尽管这最后一次的改写与扩充,已使它的篇幅增加到十倍以上,可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原有路径,故而在写作中保留了跳跃叙述要点的风格。此外,由于在公开发表这些教学的课件时,又受到了版权方面的限制,无法同时发表课堂上演示的图例,就越发使得这些文字显得紧绷起来。
当然,更重要的内因还是,自己在面对如此宏大的题目时,内心最为紧张关注的,还是它无论对我的思考范围、阅读广度、切入力度还是平衡能力,都带来了难以把握的挑战,而由此一来,我也就一直紧盯着这种挑战,很少有余力去顾及或考究文字的风格了。——前文已经坦承过,尽管这本书在篇幅上有限,可它要求的知识储备甚是广大,而且如此海量的储备,还真不是临时抱抱佛脚就能恶补的。即使你自觉得也许还能胜任,一旦沉浸到它的写作过程中,焦点也要随着论题而不停地转换,必须快速地沉潜进去又跳跃出来,所以在精神上也觉得特别吃力……
既然如此,就索性把这次时间有限的写作,首先看成对于自己“大局观”和“知识面”的考验吧!——现在斗胆把它奉献出来,正是请读者在这些方面考核一下笔者。无论如何,即使只从自己1977 年考上大学算起,这种以读书为业的生涯,也已经度过三十多年了。那么,以自己眼下的学术功力,究竟能否像高手下棋那样,既靠宏观的布局,又靠局部的妙手,既点到为止又疏而不漏地把握住“现代生活中的文化传统”,以图照顾面尽量广大、思考力尽量深入地去构想那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说实话,自己对此实在不敢太过自信,而唯一敢于确信的只是,只要我们这代人还不能想清它,就终将有负历史交付的文化使命。
如果这次很特别的写作,未能像以往那样去照顾“可读性”,也只好预先请读者给予谅察了。好在,凡是跟我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引用叶芝的一句话:“学那只母熊,把她的小熊慢慢舔大!”事实上,尽管这篇文字已被扩充了十倍,我仍然只把它看作纲目性的文字,眼下已是稍微详细点的提纲了;无论如何,相对于所要回答的宏大问题,它的分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我肯定还会像叶芝对待他的《幻象》那样,继续把眼前的这只“小熊”舔大。——比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明确地规划过,还会围绕绘画、诗歌、戏剧甚至饮食的课题,继续扩充自己对于文化因子的研究。这当然不是随口的空言,因为我实际上对于这几个题目,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发出这种总是“锲而不舍”的苦愿,并不是因为有谁在天性上偏偏喜欢这么“自讨苦吃”,而实在是因为紧迫地意识到,既已降生在这个越变越小的星球上,降生在这个日益交融的环球时代,那么,这个此身所属的、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明共同体,究竟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和命运,还可以继续拥有什么样的机会,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而且要不断重新回答的问题!——当然,下一次再为此动笔的时候,我也许会考虑另换一种表述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