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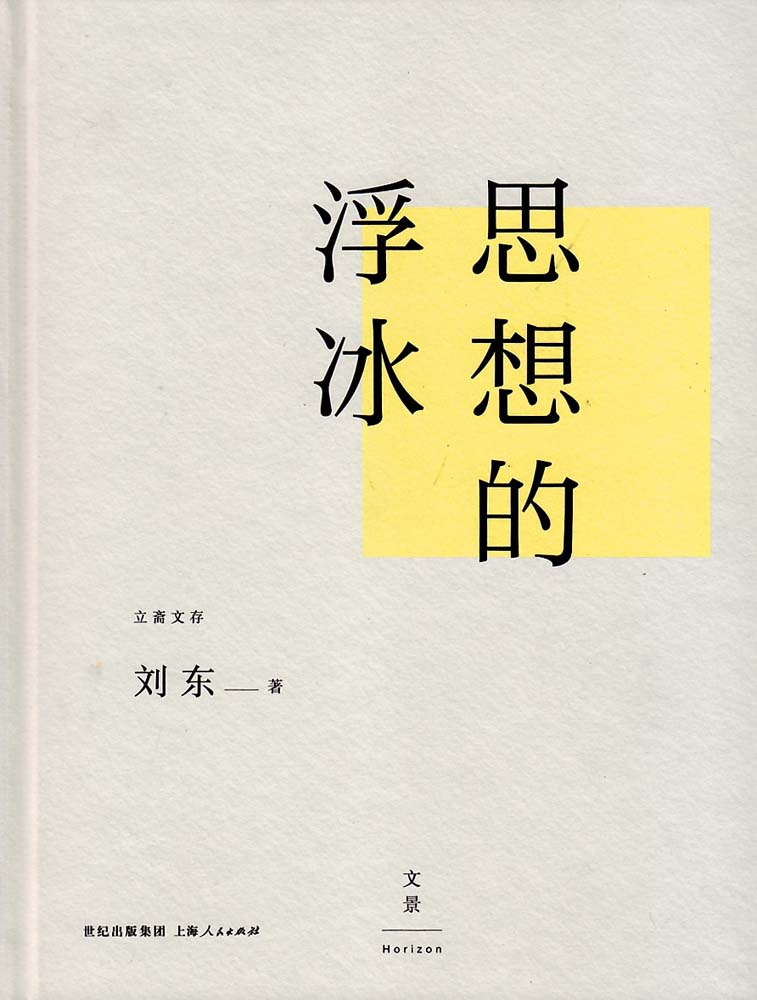 7月3日,是陈寅恪的生日。记者走进清华大学国学院,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响。“很安静,这就对了。”学者、国学院副院长刘东道。楼外的草坪上,毕业生纠结于用何种姿势拍毕业照。 7月3日,是陈寅恪的生日。记者走进清华大学国学院,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响。“很安静,这就对了。”学者、国学院副院长刘东道。楼外的草坪上,毕业生纠结于用何种姿势拍毕业照。
我们谈到“国学热”引发的种种乱象,刘东一再提到国学师资的培养困境,教育部没有“国学”学科代码,国学院正常招生无法开展。校长曾提议办国学少年班,刘东以沉默作为回答:“人心坏了,做起事来就难了。你想想,如果你9岁就被宣布是清华大学学生,是什么诱惑?我都没办法做学问了,后门要被踏破,收谁,都会被骂不公平。”老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书写了教育史上的神话。前者已不可追,如今,清华国学院重在承续一种学术精神。“国学像空气,污染了,才知道重要。如果没了,那要命。”
“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反弹”
新京报:现在谈论国学,有一个时事背景,新闻爆出国学班的孩子受到“老师”虐待,与此同时,暑期国学班、国学夏令营十分火爆。
刘东:这非常不像国学所要求的,教国学要循循善诱。国学班打孩子,你得看是不是以国学的名义在打人。想想看,非国学班就没打过孩子吗?“礼失”之后,大家想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来。“国学热”和其他的热不同,是从民间自己生发的,甚至是老爷子老太太看完《百家讲坛》,有兴趣去重新了解国学。如今社会功利滔滔,反而使得人们觉得国学很有道理,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一个反弹,不过,反讽的是,正因为利欲熏心,各方面人士都像苍蝇见血一样参与进来,国学本应该用于对这些功利心理进行“冷处理”、反思,而不能让国学也被糟蹋成功利滔滔的一部分。清华大学国学院刚成立的时候,不断有人呼吁开门招生。如果国学院能够正常招生,我想“国学热”的一些问题会被消解,但是,在现行的学科代码之下,不能培养正常的国学师资,那怎么应对社会对国学强大的需求?
新京报:还有一些成人参加的比如总裁国学班,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东:对于总裁班,也应该两面地看。我偶尔被拉去上课,有一个感觉,反而是那些总裁们最早知道国学的妙处,哪怕是人生意义这样的题目,他们都很有兴趣,放下繁忙的业务,掏出重金,参与进来。当然,他们毕竟从商业打拼的间隙中投入进来,很急,希望一块“压缩饼干”吃完就知道国学是什么,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心沉不下来,学国学还是不行。
新京报:这可能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学班的某种认识或期望,觉得那里是传习传统文化,不会打孩子。
刘东:打孩子的事,比如学体育的孩子,挨打的少吗?当然,如果以国学之名打人,认为国学就是这么专制,那就是错了。中国过去的社会,之所以还能够被容忍,并不是因为有一个专制的政体,而是有很多专制政体的劝谕者、警戒者、讽喻者,他们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教育皇上和大臣,和专制的代表共治天下,比如尚贤、使能、纳谏、考试、监察,各种制度,其实是其他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没有的。事实上,国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比较人性的那一侧面的代表。
“国学是保证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
新京报:那么,“国学热”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东:我不是“国学热”的参与者,我对于学问一直是“恒温”的。不过,我也观察到,“国学热”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玩味。首先,传统的义利之辨,至少能够约束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国度,不能用宗教的办法来约束人心,只能用道德的宣讲来确立做人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个道德并非无懈可击,否则,就不会出现“五四”运动,不会产生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了。不过,正如我多次说过的,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加在一起,才更加全面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即使有了儒家这个社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了儒家的制衡,这个社会就简直是一无是处了。更重要的是,人们还是深陷在功利之中。比如,有人来请你讲课,不听你讲“四书”,一开口就说什么“曾国藩的管理学思想”,还是想要挣钱。其实,应该从挣钱这件事脱离出来,从国学的角度来反观它。
新京报:这种乱象,正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混乱无根,需要价值重建。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能提供什么资源?
刘东:太多了。你平时想到的价值,比如西方基督教,信徒向耶和华祷告、忏悔,这算是很高的道德了。但是,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很低的境界,孔子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在我心中,由此就足以不欺暗室,自在充满,而如果非要上界有神灵看着,才能不违反十诫,那已经是不道德了。另外,国学同样强调个人自由,只是在国学的价值体系中不是最高最主要的,它还要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包括人和自我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