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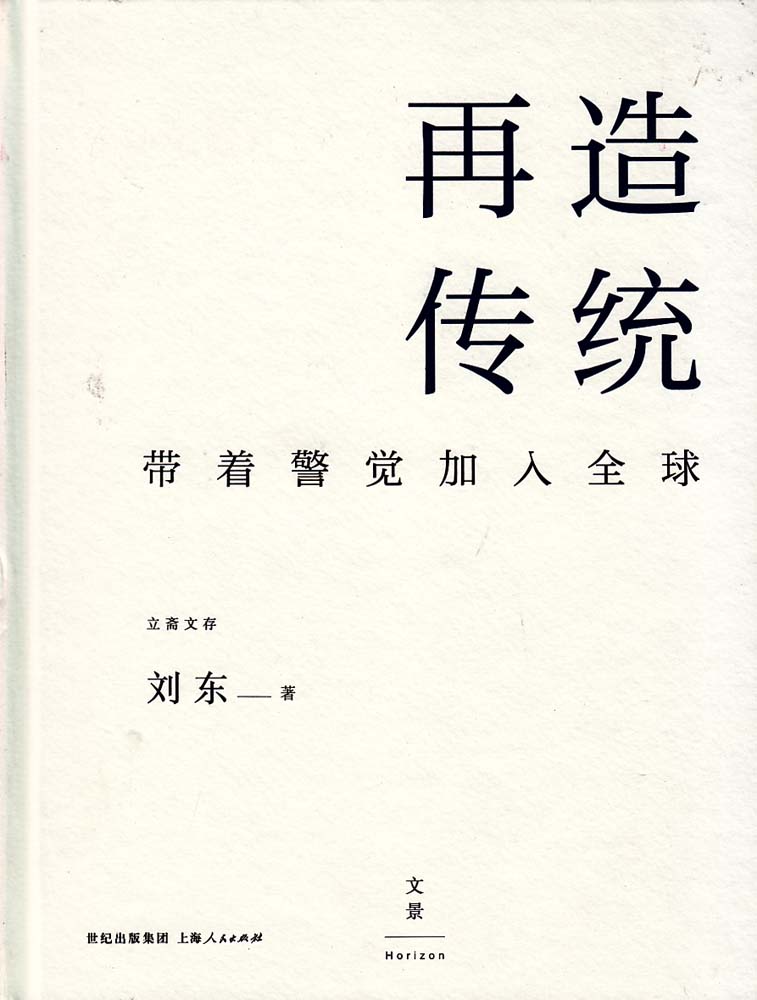 刘东教授,1955年生人,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从八十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影响持久且葆有生机。他在《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一文中提到:这三十年,自己最用心的方向,是在学术界和出版业之间钻出一个足以为己所用的缝隙,以便躲开蛮横的长官意志,成规模地组织起民间学术。而这是为了一旦有人胡乱套用时髦理论来曲解中国经验,我们知道如何“攻子之盾”;一旦实践层面闪现充满风险的危机,我们知道如何技巧地扭转历史。 刘东教授,1955年生人,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从八十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影响持久且葆有生机。他在《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一文中提到:这三十年,自己最用心的方向,是在学术界和出版业之间钻出一个足以为己所用的缝隙,以便躲开蛮横的长官意志,成规模地组织起民间学术。而这是为了一旦有人胡乱套用时髦理论来曲解中国经验,我们知道如何“攻子之盾”;一旦实践层面闪现充满风险的危机,我们知道如何技巧地扭转历史。
2009年与好友陈来合力重建清华国学院之后,刘东的思想重心发生了偏移,从更关注跨文化的对话转为更加立足本土文明的立场。全球化进程席卷而来,不可逆转,文化全球化更是大势所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备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同时,如何重建主体性,获得新生并延续活力?
若要尝试构建更加健全的中国文化现代形态,刘东认为,我们不能将传统看作奄奄一息的,只配受到保护和进行展览的熊猫,而要让它跟生猛的当代文化去厮混,去摸爬滚打,以获得并长争高的生命力。刘东坚持学术译介,继承梁启超“讲学社”的衣钵,不断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清华讲学切磋,都不外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息息相关,因此,这样的问题不应仅为少数思想者所承担,而是成为每个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都应共同致力的课题。刘东希望自己2014年6月出版的新著《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能够与更多有文化使命的读者分享自己思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危难和机遇的心得。
刘东认为,只有时刻警惕自我殖民,将全球化当作宿命来承担,我们的传统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进而,当代政治的合法性才能有所着落,人与自然的深重危机才能够和解。
眼下,刘东一心希望能够将自己毕生所思化作激情的文字,因为他的治学岁月无论如何前进,总要回到最原处的迷惑:要是连写作都没有劲头了,就不用提什么沉重的社会担当了,以学术为天职的我们,还靠什么来点燃后半段,以享受生命的辉煌火光呢?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刘东
问:你的新书《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感觉这本书是一种概论式写作,像是课程用书?
答:对。这本书有两个起因。我曾经受托撰写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的“中国部分”,加上我有次给高层上课,讲中国文化与全球化,当时写了一份近两万字的演讲稿。还有,有朋友知道后,鼓动我写一本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书。之前给联合国写报告,不需要解释什么是全球化,但换成是面对国内读者写作,我就得好好说明了。
问:“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这个主题如此庞大,用五章,十来万字能说明白吗?
答:兹事体大,涉及大小不一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只在一次课程中环环相扣地进行逻辑推演。只能点到为止,触及相应的知识点,再到课堂上即兴发挥;否则,便不可能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涉及如此广阔的领域,帮听众获得总括的、鸟瞰式的了解。第三章“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讲了八个案例:申遗,语言,建筑,电影,熊胆,体育,通识,家庭。这案例部分在课堂上最受欢迎的。在为联合国撰写报告时,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主题让我选择,我选了自然、语言、建筑和电影,这四个主题比较中性,没那么意识形态化。后来成书时我又加入了熊胆、体育、通史和家庭,作为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案例。
其实我最用力的是最后两章,前两章概述了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第三章通过案例剖析,演示了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冲击。后二章则指出了应对之策。
问:“带着警觉加入全球”,加入什么样的全球?“再造传统”,指的是再造什么样的传统?
答: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我个人认为,这种混乱的状况,正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正因为是过程,所以它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均衡,无论是哪种新颖的苗头,都有与之相反的倾向纷乱复杂地掺杂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