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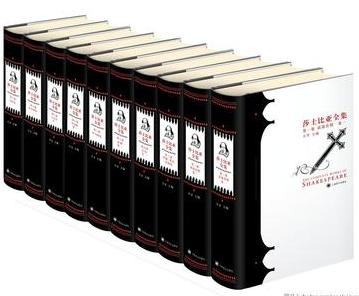 翻译家方平捐赠上戏莎翁像 翻译家方平捐赠上戏莎翁像
在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630号)上戏剧院,入场的大门旁,矗立着一尊灰白色石雕的莎士比亚半身纪念像,他头发长而卷,胡须微翘,目光炯炯有神,似在凝视,又似在神游,构思着精彩的剧本。半身像下面,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正面镌刻着大作家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底部刻着:“拿起镜子照人生。”这是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于1996年竖立的。捐助莎翁纪念像建造的,就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著名翻译家方平。
2014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了由方平主编和主译的十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方平先生已于2008年去世,在后记中,他自述道:“1993年6月下旬,开始投入计划中的全集的工作……这时我七十二个春秋了。任务重,期限紧,我可以预期的工作时间大概不会很长久了……要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这是必须要抓住的最后的机会了。”不同于之前《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这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也是唯一一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凡470余万字,充分吸收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中译的三个阶段
在2002年《深圳商报》的采访中,方平先生把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文言阶段。早在1903年,上海就曾以《英国索士比亚》的书名,以章回体的形式出版了10个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流传更广的是1904年林纾和魏易合译的莎剧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共收入《肉券》、《铸情》(即《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20个故事。这两个最早的译本都是根据英国兰姆姐弟著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用文言翻译出故事梗概。
二是白话阶段。“五四”运动后,白话文成为文艺的主流,我国开始出现用白话直接翻译莎士比亚作品。1921年,田汉翻译了《哈孟雷特》,这是正式翻译莎士比亚的开始。1924年,田汉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实秋在1936至1939年期间翻译《马克白》、《暴风雨》等8种莎剧。这些人是莎士比亚中译的拓荒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青年翻译家朱生豪开始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以每年3个剧本的速度翻译,到他32岁逝世时,共翻译完成了31部莎剧。他的遗译于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名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收录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27部,分为喜剧、悲剧、杂剧三卷;又过了7年,史剧4种才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三是诗体阶段。1944年,具有诗人气质的戏剧家曹禺,为成都一家剧团翻译了《柔蜜欧与幽丽叶》,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诗的语言去传达原作的诗意和激情、并保持原来诗体形式的莎剧译本。诗人孙大雨在1948年又翻译的《黎琊王》诗体译本,是散文译本向诗体译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解放后,莎士比亚的中译又有了新的进步。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了卞之琳、吴兴华、方平诸家的莎剧新译本,都是诗体译本。其中,卞之琳翻译的《哈姆雷特》堪称莎剧中译的经典。
让莎剧从“案头书”恢复成“演出本”
经过几代翻译工作者近百年的艰辛劳作和不懈努力,在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前,华语世界已经有了四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第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经过吴兴华、方平等校订)、由章益、黄雨石等补齐的十一卷本;第二套是1967年梁实秋翻译在台湾出版的四十册本;第三套是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由已故学者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第四套是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翻译(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正坤等校订)、索天章、孙法理、刘炳善、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推出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五套《莎士比亚全集》。
这些翻译大家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普及传播做出了不朽之功,使得莎士比亚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国作家,但是实际上莎士比亚的剧本是诗剧,而不是散文体。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是头一个华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莎士比亚戏剧的原貌是诗剧,是以素诗体(blank verse)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以前译作注重文字的雅,更像供阅读的文学作品,而这次以诗体译诗体,尽量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有望恢复莎士比亚剧作本来面目,从“案头书”变成“演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