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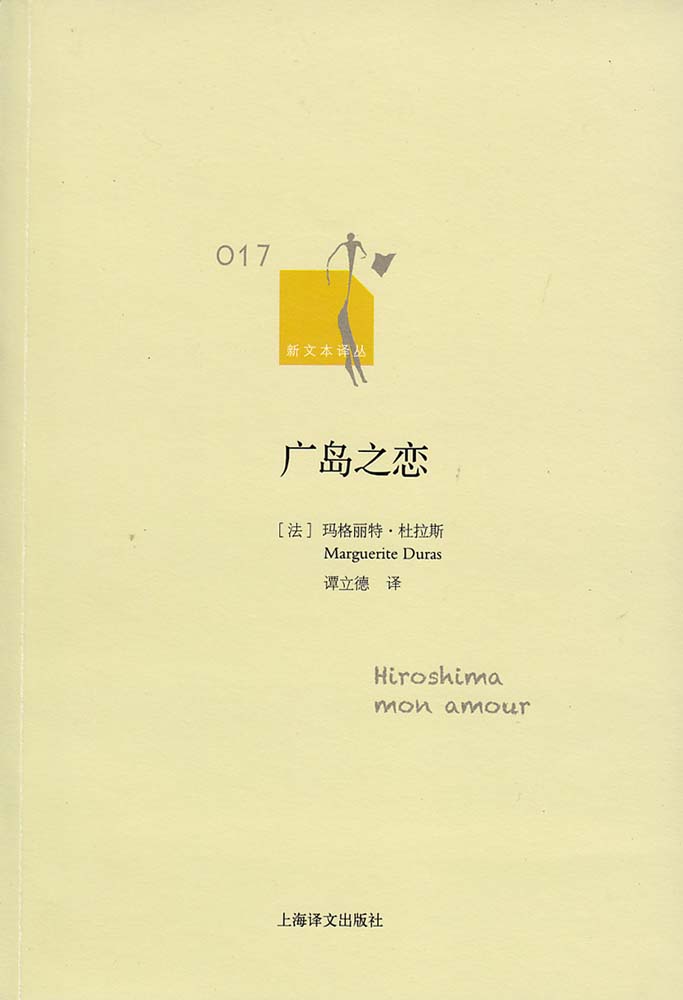 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这位苍老、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在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文革”的噩梦,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再次推动了思想和文学的“西风东渐”。和阿兰·罗伯-葛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杜拉斯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该书1958年在法国由新小说的摇篮和阵地——午夜出版社出版。 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这位苍老、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在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文革”的噩梦,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再次推动了思想和文学的“西风东渐”。和阿兰·罗伯-葛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杜拉斯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该书1958年在法国由新小说的摇篮和阵地——午夜出版社出版。
稍后,另两部杜拉斯作品也由王道乾译成中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1980),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节和结局,讲述了一个孤独的老人执着却徒劳地等待;另一本是《广场》(1984),记叙了一个女佣和流动商贩在街心花园的闲聊对话。新小说派强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中国评论界在这一文学流派面前难免有些困惑和慌张。欣喜伴随着怀疑:一方面,新小说为小说体裁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审美途径;另一方面,主人公和情节的淡化很难让习惯了传统叙事的中国读者得到“文本的愉悦”。
与伤痕文学的共鸣
1986年王道乾翻译了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学和历史反思的眼光去审视,这一翻译选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先看《广岛之恋》:《广岛之恋》的主题和风格与1980年代风行中国的“伤痕文学”有很多默契。该书中译本序的题目就是“规范之外的伤痕爱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序言作者柳鸣九用的正是“伤痕”一词来形容纠缠故事始终的存在之苦痛和悲凉。“作者的感情与立场不是‘阵营性’的,而是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城市、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生命在战争盲目的毁灭力量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她表示了一种泛人类的忧虑,一种超国度、超阵营、超集团的人道主义的忧虑,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忧虑。”
在这一确定的文学时代语境下看《长别离》,它被译介到中国也别有寓意。《长别离》是杜拉斯和杰拉尔·卡尔洛为亨利·科尔皮的电影写的剧本,该片于1961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1960年夏天,巴黎郊区的咖啡馆老板娘认定一个天天路过她家门口的失忆的流浪汉就是她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失踪的丈夫。作品中有两个非常有寓意的细节:首先是男主人公的名字,在流浪汉的身份证上,我们可以看到罗贝尔·朗代的名字,而咖啡馆老板娘黛蕾丝的丈夫的名字是阿尔贝尔·朗格卢瓦,姓名中发音的近似不言而喻,仿佛那是巨大的肉体或精神重创后记忆残存的碎片的重组。值得注意的还有杜拉斯也有过和丈夫“长别离”的经历,她丈夫名叫罗贝尔·昂泰尔姆,1944年被捕后关押在德国达豪的集中营。昂泰尔姆在集中营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后来由于杜拉斯的挚友密特朗的多方营救得以幸存回国。
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战争的伤痕让人联想到“文革”的伤痕,这两种类似的伤痕都需要被讲述,被揭露,痛苦的记忆需要再现,需要缅怀,然后才能被埋葬,被超越。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很快过时,而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因为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基于她在法国新小说探索上的建树。打动中国读者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令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
《情人》来自中国北方
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显然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译介杜拉斯的热潮:两年内出版了6个《情人》中译本,1985年3个,1986年3个)。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19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1991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确地点明了情人的身世渊源,这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中国情人的故事以坦陈往事的勇气让读者惊叹不已,那一场“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懵懂的爱情和那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的“备受摧残的面容”, 深深打动了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女性读者耽于幻想的浪漫情怀。但一直等到电影《情人》的放映,尤其是杜拉斯和她最后的情人——比作家年轻四十岁的扬·安德列亚的恋情见诸报端,才让杜拉斯成为中国媒体大肆炒作的焦点,仿佛文字永远没有画面来得触目惊心。尽管杜拉斯一点也不喜欢让-雅克·阿诺的电影,这部“少儿不宜”、经过剪辑才在中国各大影院公映的电影,以及稍后广为流传的全本《情人》盗版VCD、DVD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让很多从来没有翻开过杜拉斯的书的人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中国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