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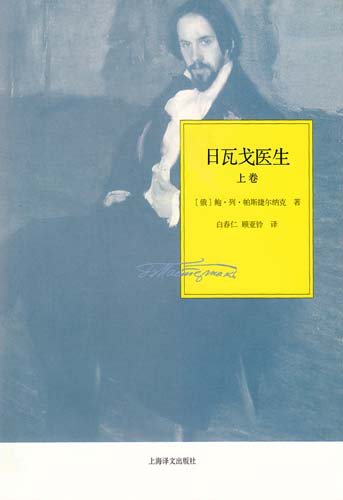 说来惭愧,虽家中藏有《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中译本,却始终没能读完。原因之一是后来看了电影,以为内容也就是这些了。2012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白春仁、顾亚铃翻译的此书最新修订版,分上下两卷,每卷封底各有两段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精彩话语。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这些话给我以震撼,也促使我读完了全书。 说来惭愧,虽家中藏有《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中译本,却始终没能读完。原因之一是后来看了电影,以为内容也就是这些了。2012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白春仁、顾亚铃翻译的此书最新修订版,分上下两卷,每卷封底各有两段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精彩话语。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这些话给我以震撼,也促使我读完了全书。
被电影遮蔽的文学杰作
以赛亚·伯林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我看来是一部天才之作,它的出版是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和道德事件。这部书在意大利出版的特殊背景,特别是,铁幕两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该书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或许使人忽略了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它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主流中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杰作,或许是这个传统中的最后一部……”当年好莱坞运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它改编成电影全球放映,算不算这“滥用”之一?平心而论,影片艺术性很强,但它把丰富复杂的小说作了简化,所抽取的又只是其中的某一层思想(而这恰是与冷战思维可叠合的部分),确实“使人忽略”这部史诗作品所含的宝贵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而且由于电影成功获得了当年多项奥斯卡大奖,众多观众在心满意足之后无意再读小说,这就造成了损失。作为当年此片的影迷,我在终于读完小说以后,深感伯林真是言之不虚,点到了要害。
伯林在另一段话中说:“这是一部非凡之作,尽管它的开头使人困惑,象征主义的手法时时让人捉摸不透,结尾又充满了神秘。用来收尾的那几首绝妙的诗歌用英文也很难转达。但无论如何它不失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表现力到今日也无人企及。”这是非常诚实的评价。应该说,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很不少了,但几乎没见谁这样坦论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细读之下,很难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规范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圆熟练达之作。这是诗人的小说,前半部由于要表现的内容太大、太多、太宏伟,他的笔有点应付不过来;后半部又由于对故事有太多太久的酝酿发酵,感情太烈,急切而不能已于言,有的地方太浓而有的地方太简(当然有些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含蓄)。全书开头,历史画面极为开阔,人物事件多头并进,而每一头都只寥寥几笔,须非常用心才能读得进并记得住。伯林说的“象征主义”是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西方文论的常用语,涵盖面非常大,如三十年代美国大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其《阿克瑟尔的城堡》一书中,就将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与维里耶的诗剧《阿克瑟尔》等都归入“法国象征主义”。他对象征主义的解释,是“抛弃了逻辑与清晰的传统”,追求一种“与音乐相仿的不确定性”。可见,那时是把包括意识流在内的大量有别于传统的新表现手法统称为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曾是与马雅可夫斯基齐名的象征派诗人,他最后这部小说则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伯林所指的,也就是他的有些描绘不够“逻辑与清晰”,他确是常常追求“与音乐相仿的”抒情性或那种含蓄暗示的效果,只缘于他对这一题材充满特殊情感,也缘于他诗人天性难以压抑的流露。作者有时写得极投入,有时又显得太匆忙。但这毕竟是一篇多事之秋的大时代史诗,在这样的乱世,多少人的踪迹到后来真的只剩了一星耳闻。而诗人的特点就是将情感集中到他最感兴趣的点上,在这些地方爆出审美的极致。所以,伯林还说过:“但小说对公众欢迎二月革命的描写却极其精妙;当时我七岁,正好在彼得格勒……帕斯捷尔纳克把对此的描述提升到一个天才的水准……是我看到过的最生动的描述。”是的,它就是一部非规范、却具有非凡表现力的杰作,我在读完小说后,觉得真要拿什么作品相比,倒是中国的《红楼梦》略有几分相像,《红楼梦》也不规范,虽然结构精巧之至却并不完整,中间的错漏及那种草稿的痕迹也时或可见,然而它的天才的杰出的部分恰恰是任何规范之作所无可比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