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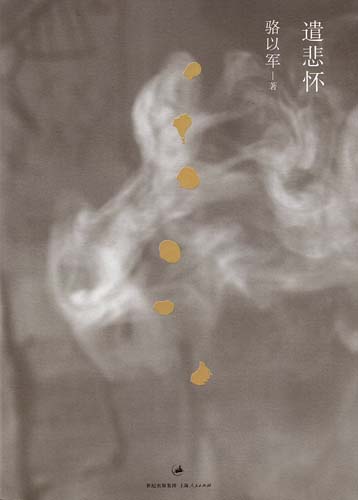 黑格尔预言“诚实的灵魂”将被历史唾弃,而“分裂的意识”会节节获胜,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此已作出了无数的印证。邱妙津的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的人,她和她的死成为另一个充满写作激情者的捕食对象,被后者撕裂、观看、思索,又被献上祭台。在这样一个写作的祭台上,死亡变成景观,写作者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亵渎。 黑格尔预言“诚实的灵魂”将被历史唾弃,而“分裂的意识”会节节获胜,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此已作出了无数的印证。邱妙津的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的人,她和她的死成为另一个充满写作激情者的捕食对象,被后者撕裂、观看、思索,又被献上祭台。在这样一个写作的祭台上,死亡变成景观,写作者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亵渎。
从里到外都顶着哀悼亡友邱妙津之名,并展开所谓“生死对话”的《遣悲怀》,当初在台湾出版后,激怒了一大批邱妙津的拥趸,认为小说是对邱妙津的意淫和亵渎,尤其在亡者无法开口的情况之下。然而,去年《遣悲怀》在内地出简体字版后,这种愤怒令人惊讶地没有重演,仅仅被淡化成一种女同的情感创伤,抑或成为执掌虚构大权的小说家遭遇真实世界压力的又一个辛酸案例。可以说,《遣悲怀》在内地激发的,迄今为止,依旧是一边倒的对骆以军小说技艺的膜拜。
的确,在《遣悲怀》中,骆以军的小说技术呈现出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成熟与自由的姿态。他的叙事每每启动于平凡细微处的日常遭遇,甚至只是一个人静坐时的散乱思绪,却能经由其叨叨念念般的叙述,飞快地达至某个诡秘高度,随后,没有随后,像是置身一个构筑在悬崖之上的蜂窝状迷宫,他带领你鬼魅般穿越一个个房间,忽然他就消失不见,你推开面前唯一的一扇门,一脚跨出,是浩荡到令人眩晕的碧空。
倘若小说当真只是隶属于时间的技艺,那么《遣悲怀》确可以被视作一次技艺展示的典范,一座时间的迷宫:“那里头有许多‘处于不同时刻之当下’的人物、街道和房间,他们全都不是处于静止状态的静物画,而是处于一种时间的倾斜状态。它们的内部,都有一种画面无法支撑的、时间的歪斜。有的向未来倾斜,有的向过去倾斜。当我在描述它们时,它们被拘在这一个状态里,但是当我叙述停止或一转身,悬住它们的那一丝暂时状态便被切断,它们就会朝向那个倾斜的姿势哗哗崩毁……”这段由《遣悲怀》的叙述者“我”讲给邱妙津听的,对想象中完美小说的描述,用以描述《遣悲怀》本身也无比贴切。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并非源自死亡和追悼,而是源自作者与邱妙津的一次短暂邂逅,在那次邂逅中,他们描述各自的小说理想,日后《蒙马特遗书》和《遣悲怀》作者迥然不同的小说理想。
在我看来,邱妙津拥趸乃至邱妙津本人,与骆以军之间在小说认识上的冲突,几近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谈到的,“诚实的灵魂”和“分裂的意识”之间的冲突。邱妙津的小说人物有着高度的生存意义,意味着自我的定义,意味着对生命的诚恳要求;而骆以军的小说人物则是分裂的旁观者,是丧失自我生活的人。黑格尔预言“诚实的灵魂”将被历史唾弃,而“分裂的意识”会节节获胜,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此已作出了无数的印证,但随之而来的吊诡在于:那些在当下依旧顽强幸存的少数“诚实的灵魂”会生活得无比艰难,并在强大的时代压力下渐趋分裂;而那些如骆以军一般对“分裂的意识”保有内在认同感的当代人,因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反倒弥散出一种基于诚实的安宁,我分裂,故我在,于是荒怪与美善一体,淫猥和纯真并进,生命转而成为一种单细胞分裂式的弥天弥地的华丽景观,思辨和观看代替了具体的生活,不再有集聚自身的生命,不再有朝着某个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生命。
在邱妙津那里,写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为了不能完成的更好的生活;而在骆以军这里,生活是为了更好地写作,他有如我们时代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常的经验匮乏者,只是为了写作,他需要比常人更贪婪地捕食生活经验。邱妙津的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的人,她和她的死,成为另一个充满写作激情者的捕食对象,被后者撕裂、观看、思索,又被献上祭台,而这一切又都统统顶着现实生活好友和文学虚构创作的神圣名义,堂而皇之的呈现,洋洋自得的呈现,带着一切所谓后现代哲思面具的呈现。在这样一个写作的祭台上,生活变成景观。死亡也变成景观,写作者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不再有真正严肃的生活和写作,也不再有真正严肃的敬畏与悲伤,这才是这部《遣悲怀》真正令人不堪的事实。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亵渎。
作为对照,我们可以看一下邱妙津好友赖香吟在邱妙津自戕之后的反应。赖香吟是邱妙津同年同校的死党,是其最后时刻的通话者和遗嘱交代人,也是一名同样才华横溢的写作者,她本来有足够的素材和理由来书写亡友,但她长时间以来只是默默整理亡友的笔记本和手稿,在事隔十二年后,才终于编辑出版《邱妙津日记》,在序中她说:“我无意多言妙津其人其事。关于悲剧的发生,很难有人能说清楚始末因由,也没有人有绝对的代言权。我只能接受,伤害千真万确发生,死亡无可挽回。”她另有一篇《十年前后》的感怀短文,以接待邱妙津家人参观台湾文学展为主线,尽诉十年生死苍茫,却也不曾直言邱妙津其名,而是将之化名为“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