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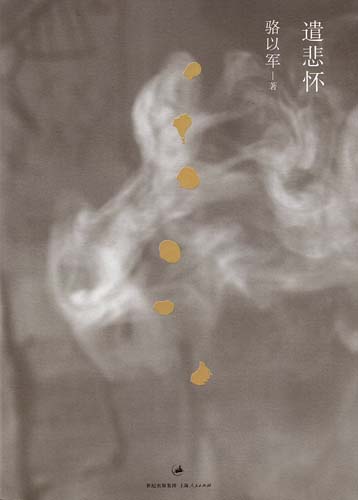 他暗中“窃取”他人的故事,“笔如刀,被处理到的人,都鲜血涌冒。”作为外省人,他一出生便没有了味道,便成了小说《香水》中,那个不顾一切索取各种层次味道的格雷诺耶。 他暗中“窃取”他人的故事,“笔如刀,被处理到的人,都鲜血涌冒。”作为外省人,他一出生便没有了味道,便成了小说《香水》中,那个不顾一切索取各种层次味道的格雷诺耶。
魔性作家
读骆以军的小说,读者容易出现如下症状:噩梦连连、呕吐不止、干嚎大哭。仿佛故事一流过他的身体,便充满猖獗的魔性。台湾读者称其为“变态小说家”。
出道二十余年,近十部作品满目皆是令读者心生恐惧的遣词造句能力、狂乱想象力与隐喻。他当然是讲故事的高手,但那些画面总被塞在差异化的时空,消解宏大叙事后,他将拼图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更不论其笔下颠乱的性与暴力。被肢解的尸体、杀妻者……万花筒般的伤害朝读者汹涌而至。“我们造的字覆盖不住新发明的各种杀人方式。”
朱天文曾一语中的—骆以军的眼睛就像核爆,所有东西被他目光一扫就全部变成废墟。
近期密集的推书活动中,当不少带着“文如其人”想象的大陆读者看到这只谦卑、憨厚、傻笑的“玩具熊”,难免在微博上大呼:“原来骆以军这么萌!”再听其满嘴白沫地倾泻或黄或暴力的段子,读者们又印证了原初的概念,“他就是个爱叨的疯子”。
很少人相信体形虚胖的骆以军是个吃素的,同时也会惊讶于这位以伤害为小说核心的作者是晕眩症患者。
“儿时常被母亲丢在一个杀鸡店门口,目睹无数鸡脖子被扭曲或割断的惨状,从此谢绝鸡肉。十九岁考大学,成绩很烂,去一个佛堂拜拜发誓吃素。”
也许跟暴力的语言内容反差太大,骆以军总乐呵呵的热情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悦然给他算星盘,结果是:“很有同情心且善良”。“这是个悖论,如果我会揍我的小孩,那也是因他试图伤害别人。”骆以军说。
最是难堪的,不过是现实中人给人带来的羞辱。被朱天文形容“全身都是敏感带”的骆以军,曾在办公室呆过一个月,“被压迫者压迫人的微观政治”让他几乎崩溃,离职当日,一路开车哭回家。“对我来说,一个空间里,两个人跟三个人也很不一样。除了写作,我就是个废人。”
出于恐惧,他极度有礼、谨慎。台湾作家袁琼琼写道:“骆以军开着车,但只要我跟他说话,他就恭恭敬敬地转过头来,眼睛注视着我,很慎重地回答。拜托,我还想活咧!”直到二十八九岁,骆以军跟长辈去聚会,从头紧张到尾,晚上回去后脑袋倒带式地重播,反省自己是否有讲错话或自鸣得意。
这种紧绷的道德感及羞耻感,也许来自骆以军家中的佛龛和永远板着脸的父亲。骆以军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父亲则异常严肃。他在讲述父亲故事的《远方》中回忆少年图景:幼小的眼睛望见父亲赤裸庞大的躯体,父亲一直以为天经地义地将一封封已拆私过目的少年信件递给自己的儿子。
做错事,哪怕小小的谎言,骆以军也惶恐于母亲房门的神,或父亲口中遥远的大陆祖先都会给他致命的惩罚—也许会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我六七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小孩,躺在床上哭到枕头湿透。想老天为什么不让我做个好人。”
一颗年轻的自卑心反而激出了伤害的念想。“考试前去佛堂拜拜,结果考差了,我回家自渎,内心怨恨神—你不实现诺言,那我就伤害你安排在世的肉身。”
王德威似有所感,为其作品《遣悲怀》作序,标题取作“华丽的淫威与悲伤”,“他是一个对身体和情色非常不敬的作家,但是你读他的小说,真的会感受到他深沉的悲伤,越读,你越会不忍。作家只有将自己作践成那样,才能呈现出这样的文学。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文学。”
与其笔力对应的是,骆以军确实着迷于观察、刻画残忍。“在路上看到一只被汽车压烂的猫,心里很悲伤,但满脑子都是如何将这死亡的惨状铭记下来。”包括尚在早期阅读中,他也无法接受《追忆似水年华》的柔美感伤,只一头钻进凶猛暴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太宰治、福克纳的世界中。
作为星盘高手,骆以军无法解释自己的命:“到底是因为我内在住着一个暴力的恶魔,所以我一直用道德感把它镇住,还是我用恶魔来掩饰内在的天使。”
不管如何,这位“魔性作家”的新作《西夏旅馆》中爬出了很多长毛的动物。同样着迷于星盘的张悦然归纳骆以军的审美倾向,“他喜欢那种破的、烂的、倒霉的、短命的,然后那种动物性的、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每个字都长着毛。”
至于大陆读者“质问”其何以如此“变态”,骆以军为之喊冤,“好像我是石头里迸出来的变态。大陆读者对我的作品还不够了解,《西夏旅馆》的本意要趋近凶猛的变形怪物,才出现大量关于生殖、原始暴力的隐喻。像《妻梦狗》的运动感、光线就比较柔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