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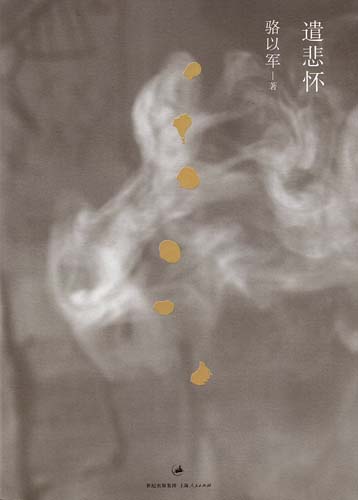 在很多有文学阅读习惯的读者那里,大概存在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汉语写作总是显示出一副跟不上趟的姿态。尽管文学不能用领先或者追赶来形容,但汉语文学的整体落后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因为这种共识下的落后,才有那么多人的不甘心、追求和鼓吹。近些年大量引进港台作家作品就可以看成这种不甘心的一种市场表现。从商业角度来讲,书商认为这是可以谋利的一种方式;从供需角度来讲,正是刚才说的落后和不甘心才使这些引进作品有了消化空间和市场份额。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身边这些作家节节败退,那么海峡对岸的台湾和一墙之隔坚持一国两制的香港,会不会有惊喜存在而我们不知呢? 在很多有文学阅读习惯的读者那里,大概存在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汉语写作总是显示出一副跟不上趟的姿态。尽管文学不能用领先或者追赶来形容,但汉语文学的整体落后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因为这种共识下的落后,才有那么多人的不甘心、追求和鼓吹。近些年大量引进港台作家作品就可以看成这种不甘心的一种市场表现。从商业角度来讲,书商认为这是可以谋利的一种方式;从供需角度来讲,正是刚才说的落后和不甘心才使这些引进作品有了消化空间和市场份额。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身边这些作家节节败退,那么海峡对岸的台湾和一墙之隔坚持一国两制的香港,会不会有惊喜存在而我们不知呢?
这样美好的愿望下,大量一二三四五流的作品被打包成汉语经典、被遗漏的不朽、华语世界的巅峰等等纷纷出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读者,一开始我也满怀期待,真觉得港台藏着无数个张爱玲、夏志清,他们早就在写,但一直被蒙蔽和遮掩。但实际上,无论是经过阅读的验证,还是如今已成泛滥之势的港台作家作品所呈现的状态,他们显然都没经得起这样的期许。出入媒体的名流被包装成文化大师,普通读书人获得话语权之后被臆想成高级学者,三流作家被市场催生成汉语文学的拯救者,市场化的文字工作者被广告美化成一代巨匠,不入流的写手被媒体一点点塑造成语言、意识形态高手……
除去书商为了“卖”而不得不吆喝出来的那些肉麻宣传攻略,我们的读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港台作家拔苗助长风潮中起到了太大的负面作用。不明真相,轻易感动,泛滥爱意,将善意变异成轻浮、廉价的阅读感受,我们读者在贡献腰包中的书报费之时,也又一次地拖拉了汉语文学有可能进步的脚步。
不能只说现象,要举例说明,甚至为了论证还要一件件扒光刚才所提及作家的外衣,让人们看看他们光鲜的被包装的外表下藏匿的是怎样的平庸和廉价……但你知道,这样做无论怎么有道理,最后也会被人说成主观之下的一己之见,得罪人的事总是经不起质疑。况且我又不是方舟子老师,从浩瀚的文字中可以找到符合自己臆想的“蛛丝马迹”。但不举例,脑海中萦绕的那些曾让我上当过的“矮矬穷”式的作品就挥之不去。这样吧,我只负责举例说出结论,不论证,到时候你们不同意,怎么反驳我都接受。视野之内,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马家辉的《明暗:源于影像的微琐絮语》、《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梁文道的《噪音太多》,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公寓导游》等等,这里有的是言过其实,有的只能是个笑话。
从质量上来看,就自己的阅读范围之内,蒋勋的《孤独六讲》,张大春的《离魂》、《小说稗类》,骆以军的《遣悲怀》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他们的问题大概不在于写的东西不够好,而是大陆书商对他们的过度开发,让读者只能擦亮眼睛再戴上放大镜去选择真正的作品。
从文学最原始的意思出发,阅读小说,从中进行审美和欣赏其多变的手法以及独特的态度和价值观,骆以军的《遣悲怀》倒真的可以称得上填补大陆文学的某个空白。骆以军有着神乎其神的语感,他可以将庸常的行为嫁接到虚无的想象中,再将两者糅成一种需要慢读的复杂从句,给予读者的是纠结和意犹未尽的双重阅读快感。
跳过骆以军给人超出想象的文字美感和故事的真实死亡背景,以及显然需要多费点脑子去贯穿和理解的小说结构,我们单从小说的最基本形态,即语言+故事+态度来看他的《遣悲怀》,我以为这里还是充满难以言说的快感和敬意。并非玄虚到需要用诗意来解释,而是直截了当地阅读、理解和参悟,也能从这部短篇小说集找到各种类型读者想要的。作家本人通过语言暴发户式的宣泄,留下的两种客观存在的印象也难以磨灭,所谓正与反、赞与弹,对于骆以军的这部小说都是无法靠一方就轻易将另一方抹杀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