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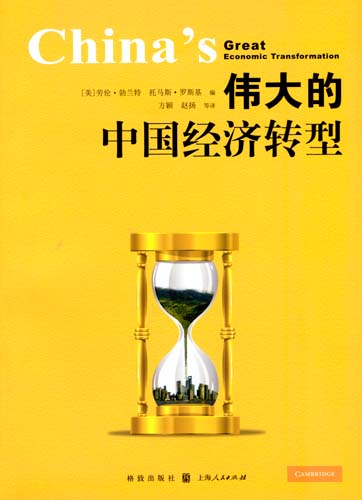 陈冠中的《盛世》夸大了中国盛世“嗨”景,但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的描述却相当准确。2009年,“危机”一词占据了所有核心的经济学议题,危机的成因,危机的过程,危机的应对,未来危机的防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陈冠中的《盛世》夸大了中国盛世“嗨”景,但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的描述却相当准确。2009年,“危机”一词占据了所有核心的经济学议题,危机的成因,危机的过程,危机的应对,未来危机的防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分析2008年以来的危机成因,奥地利派、芝加哥派、凯恩斯派各自施展绝活,鏖战至今也分不出胜负,分歧已经被标定在从右至左的理念数轴之上。但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真正原意是否如此泾渭分明,还是只是因为被贴上标签,导致各自强化,混战在无边的理论黯野。正如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所说,批评这种简单化的指称将会削弱丰富性和多元化,进而被命运的幻象笼罩。而单一化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泥淖。
动物精神
廓清凯恩斯到底说了什么,实在并非可有可无的努力,尤其是在全世界的救市方案都被标记为“凯恩斯主义”及其各种变形时,更是如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的《动物精神》正是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新时代呼应,当然还有拓展。
阿克洛夫和希勒将凯恩斯的《通论》与古典经济学对照,发现凯恩斯采用了更加务实和中庸的理论之道。凯恩斯承认,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这些行为人“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从事市场交易,增进各自福利。但凯恩斯也认为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也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总是理性的。而这种“动物精神”正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因此对于政府这位市场的“守夜人”来说,要维持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重要的是设定一些规则来约束过度的动物精神,但也不能像古典经济学一样对动物精神视而不见,认为人类总是像机器一样理性。因为不约束动物精神,贪婪就会驱动狂热,任资产泡沫越吹越大。而一旦有一个微小的因素刺破了泡沫,动物精神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恐慌”,进一步加剧动荡和不确定性。
可惜的是,凯恩斯的上述“动物精神”观点被扔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凯恩斯也变成了政府应包办一切的利维坦支持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明白指出,凯恩斯没有那么极端,正如哈耶克一样。那些脱离常识和日常生活语境的“理想类型”只是大师的“思想体操”,他们并没有暗示这些“理想类型”应该用来指导“真实世界”的经济政策,那些不过是罗斯福们或者里根们的政治选择而已。
因此应重提动物精神,并用此解释本论金融危机,贪婪到恐慌的心路历程符合动物精神的解释,而政府的角色是约束脱缰的兽性,但也不禁锢天性的好奇带来的创新。政府的作用是让这两种不同的动物精神都不要太过,使得市场失去监管后反噬参与者的福利。
死灰复燃
实际上,沈联涛就尖锐挑明了这一点。在真实世界中要做一个选择,多少要权衡取舍各方的利益,最后不可避免地趋向中庸之道。沈联涛曾出任1998年至2005年的香港证监会主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正担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他的亲身经历是:当前经济危机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华盛顿共识告诉我们不能做的,包括干预市场、降低利率、放松财政管制、允许银行破产来扼制道德风险、停止卖空交易和谴责操纵市场行为。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沈联涛此书的标题解释了他的用心和意图。首先是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因及其后续的拯救措施进行剖析回顾,其次是对照2008年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后续拯救措施。世事已是沧海桑田,政策依旧轮回变迁。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危机前的情形看上去总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股市房市屡创新高,流动性充足,风险溢价降到历史冰点,所有人都“嗨嗨”的。然而,正如叶芝在《死灰复燃》一诗中所写:万物崩溃,人心已散,唯有混乱,漫无止境。血色潮汐,淹没纯真,善念不存,恶意狂盈。危机来临时,到处都是这种恐慌。
沈联涛从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朴实但关键的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尔后的改革难道不足以防范新的危机?金融监管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所有危机都是从流动性过剩开始的,接着出现投机热,然后形成泡沫,最后发生崩溃。不同的是,十年之后,世界经济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一国两制”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思路。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捍卫市场的作用,但危机的确发生了。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虽然能部分解决分配公平和产权保护问题,但无法避免为国家机器利用而导致过度监管的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新困境是,各国实行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却忽略了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外溢效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里提到的“中美国”模式,恰是这样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