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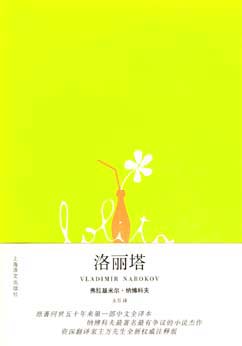 早就想写点什么,可又一直觉得我或许不是最适合说这些话的人,而且说了也未必有意义。最近网上又有人问起,不少读者还有误会。我想,既然热已经热过去了,说说大约也无妨了吧。我首先承认我的译本的确存在很多“硬伤”,朋友们和网友们提的意见都很中肯。我的意思是,我不打算为自己辩解,也不想批评什么,只是想就我所知对两个有误解的事实做个说明,同时也发个小小的“牢骚”。 早就想写点什么,可又一直觉得我或许不是最适合说这些话的人,而且说了也未必有意义。最近网上又有人问起,不少读者还有误会。我想,既然热已经热过去了,说说大约也无妨了吧。我首先承认我的译本的确存在很多“硬伤”,朋友们和网友们提的意见都很中肯。我的意思是,我不打算为自己辩解,也不想批评什么,只是想就我所知对两个有误解的事实做个说明,同时也发个小小的“牢骚”。
网上说的最多的是——是否“全译”的事。上海译文版《洛丽塔》有句响亮的宣传词,说他们的译本乃“原著问世五十年来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这个说法我不能同意——这明显是在误导,好像非要让读者认为我们先前的译本都是“节译”才能体现他们的意义(我不说“价值”这个字)。可这不是事实。起码我的三个译本(江苏文艺1989年版,时代文艺1997年版,译林2000年版)都没做过任何删节。南方的一家报纸曾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过“没有什么可删节的”的话。的确如此,如果看过原著的人一定都知道,这本书从字面上看其实很干净(意思如何可以仁者见仁),里面没有任何不能译出来见人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做任何删节。
许多人问为什么主万先生的译本会比我的译本多出那么多字?撇开任何宣传词不谈,事实应该是,除了先生的行文风格与我不同、对小说部分的翻译总会有一定字数出入外(但这个出入一定是很有限的),他的译本多出的字数主要是在注释上,也就是说,他增加的是注释而非小说本身多出了那么多字数。
第二个误会便是这个注释。许多读者认为主先生译本里的注释是先生自己做的,这是很不准确的。我不知道读者是不是受了先生译本上另一句响亮的宣传词——“翻译家主万先生全新权威注释版”的引导而得出的结论,但我思忖总会有一定关系。出版社在“谁做的注释”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完整的信息。
了解《洛丽塔》原著版本的读者或许知道,在《洛丽塔》写作完十五年后的1970年,V intage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个《洛丽塔》的注释版本。这个注释版本,跟纳博科夫的另一部作品《微暗的火》不一样,里面的注释不是小说本身的一部分,作注的人也不是纳博科夫本人,而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阿佩尔的学者。这个人1934年生于纽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从他的注释看,他与纳博科夫有过交往,许多注释都直接来自纳博科夫本人的解释,所以,是很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洛丽塔》的学者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对一般读者理解作品也有意义。因此这个注释版本后来几经修订多次再版,成了最受欢迎的《洛丽塔》版本。
我做了一些核对,主先生版本里的注释,绝大部分便是节译自这个注释本。也就是说,先生的注释大部分并非先生本人为小说做的注,而是译自英文注释。
实在说,我的时代版和后来译林版里的不少注释也是节译自这个注释本,但并没译全。一个原因是注释太多了,注释部分几乎有小说部分的一半厚,要全部译出,几乎等于再译一本书,而且是一部学术著作,其难度不亚于译《洛丽塔》小说本身,可能更甚。主先生的译本也是如此,他也只是做了节译,离“全译”还差得很远。比如“第一部”里的第一个注,关于“洛丽塔”一词,原注有整整一页那么长,很详细地讲了这个名字的由来,纳博科夫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等。而主先生只译出了原注的第一句话,即“‘洛丽塔’这个名字是本书《序文》的第一个词,也是这部小说中的第一个词和最末一个词。”但这句话并不是先生的话,而是阿佩尔的,是先生译的。如果主先生能把阿佩尔的注释“全译”出来,那全书的字数恐怕五十万都不够。再说我,我当年没有全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也考虑到了版权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已开始有版权意识,知道注释是别人的心血不能随便使用,但还没有足够的版权商业意识,不懂得应该让出版社买下注释版本的翻译权,以免除不必要的纠纷或麻烦。因此,我只在时代文艺版的译后记里对注释本做了比较仔细的说明,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注释版本的存在,并向注释者表示了感谢。
在看到这次上海译文社的新译版本之前,我先在网上看到他们的宣传词,便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买下的版权应该是阿佩尔的这个注释版本的版权。但等后来拿到书查看了他们的版权页后,才感觉似乎不是。是不是也许并不重要,但让我比较吃惊的是,虽然主先生译介了大量阿佩尔的注释,但这部译著从头至尾没有提到这位原注释者一句,读者想当然地以为那些注释是主先生做的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误导其实完全应该、也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