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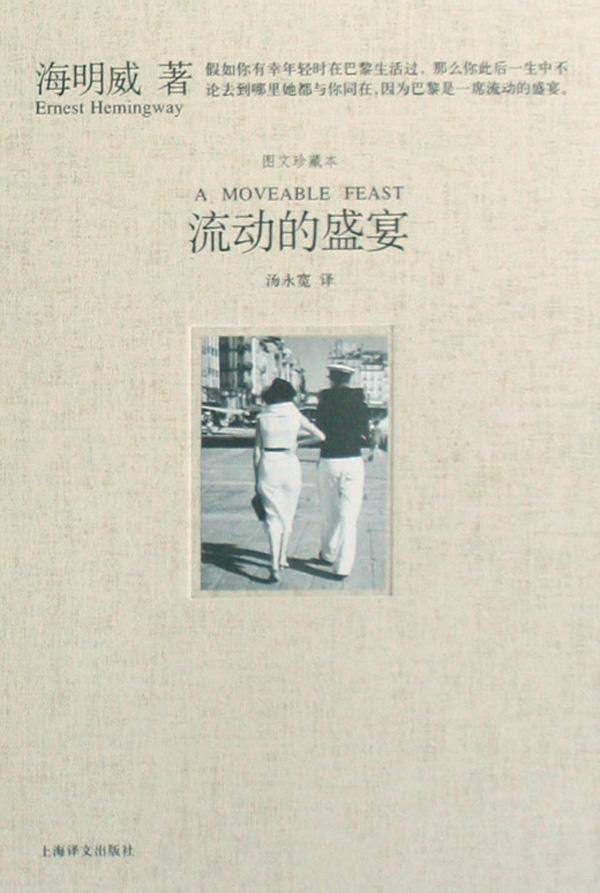 海明威1921至1926年消享花都风月无边,赶上了法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痴狂岁月”,他的回忆是“虽嫌贫寒,但有好书读,有好饭吃,有好事忙,真如得了座大宝库一般”。普利策奖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莱许就说,这六年为海明威的时代开创了一种文风。 海明威1921至1926年消享花都风月无边,赶上了法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痴狂岁月”,他的回忆是“虽嫌贫寒,但有好书读,有好饭吃,有好事忙,真如得了座大宝库一般”。普利策奖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莱许就说,这六年为海明威的时代开创了一种文风。
海明威与哈德莉
据说,把文学的水分蒸发净尽,只剩下爱情、战争、死亡。三样干货,海明威大卖特卖。《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此题随俗“误”译,恕不赘)是他自杀后第一部由未亡人整理出版的书稿,和上述三样都不大沾边,不在他最出名的作品之列。
但其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作者否定其回忆录性质的回忆录型作品。已故译者汤先生在《前记》中将此书缘起交待得很清楚:“由于电震疗法,他(暂时)丧失了记忆力。这自然不能不使他产生生命将尽的感觉,回顾往昔,而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1957年,他找回了1928年落在巴黎丽姿(Ritz)酒店的整箱子私人文书。关于真实性,海明威则在自序末尾说:“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的那些事实的。”近半百年来,早有美国文学史学者指出,《流》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虚构又分主动、被动两类,前者足证笔力尚健,后者只缘脑力不济。这样一部作品,便不单单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或“创造性的回忆”(钱默存先生语)一句可以概括的了。加之作者的第四任夫人玛丽·韦尔什诓称“不动只字”,暗地却大规模“校订”,将先夫原来章节的排列打乱,统以时间为序,又阴发醋兴,删去各稿均存的致发妻哈德莉的道歉文字,代之以自撰的《说明》,全书的匡庐面貌遂越发朦胧。如此编辑,未必每个读者都叫好。蒙大拿大学的盖瑞·布莱拿就颇感不平,遂将约翰·F. 肯尼迪图书馆内所贮海氏生平资料详加考据,写了篇论文,题为《我们赴的还是海明威的‘盛宴’吗?》。不过,海明威掌勺的“盛宴”,据Routledge书局1997年版的《海明威:评论汇编》说,是“文多毒汁,字极狠刻”(venomous and brutal)——除了当时的老婆,他把周围人写得几乎都不咋的,或者说,并不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光辉吧。
《流》又一重魅惑力,在于背景不是别地,而在花都巴黎。无论是小资,抑或文青,“巴黎”二字,一如李公明先生所言,“发音本身就蕴含有无穷的魅力——分开来,毫无美感;合起来,‘巴黎’,真是妙不可言”(见《上海书评》2008年12月21日《谁是真正的……盗火者?》)。稍解风情的男子,哪个不是让香奈儿广告里妮可·基德曼那回眸一瞬,撩拨醉了,恨不能时光倒转一百年,屁颠颠跑到“红磨坊”门口做个穷诗客?“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就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这并不是旅行社广告式的煽情。海明威1921至1926年消享花都风月无边,赶上了法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痴狂岁月”(les années folle),他的回忆是“虽嫌贫寒,但有好书读,有好饭吃,有好事忙,真如得了座大宝库一般”。普利策奖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莱许就说,这六年“为他(海明威)的时代开创了一种文风”。
《流》的“回忆”无不围绕着当时有头有脸的文化人物,故这边就有人很夸张,说此书是西方当代的《世说新语》:诗坛教父、晚年扣上“法西斯主义者”帽子并锒铛入狱的埃兹拉·庞德;长相打扮活像福尔摩斯的T. S. 艾略特;讨了一房多事的娇妻,以致英年早逝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早前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一译《灯绿梦渺》)著称,最近因《本杰明·巴顿奇事》(改编的电影作《返老还童》)重又走红;积极拔擢后生晚辈因而影响力及于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等一代英髦的舍伍德·安德森,就是他建议海明威以驻地通讯员身份来巴黎闯闯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办的《大洋两岸评论》常登载海明威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文章,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太阳依旧升起》(港译《妾似朝阳又照君》)里,把他处理成一个配角:“辞气堂庑甚大,而于云雨妙处,多不能传其真”的英国作家布拉多克斯;还有那位装束如意大利农妇、脾气如亚平宁农夫的“大姐大”葛特路德·斯坦因小姐(其实是阿婆),据说此人褒贬文学新锐,华衮斧钺,难怪日后的大胡子文豪在她面前总似个小学童,执礼谦恭……是呀,那时的巴黎,海明威充其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咖啡馆里发现乔伊斯夫妇在邻桌用餐,“高山景行”只能偷窥几眼,半是惊喜,半是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