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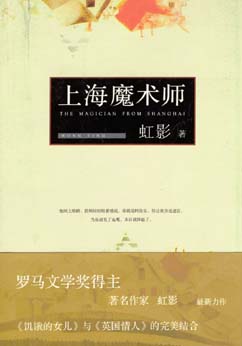 看虹影变“戏法”,让人捏把汗。倒不是说她变得不巧、不妙,而是瞧着费劲。当然,这里的“戏法”,不是什么“大变活人”、“空中飞人”,而是指“小说”,也就是“讲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讲故事的人”和“变戏法的人”的确有点像。他们都借着某种技法来营造一种有别于平常现实的“奇观”。 看虹影变“戏法”,让人捏把汗。倒不是说她变得不巧、不妙,而是瞧着费劲。当然,这里的“戏法”,不是什么“大变活人”、“空中飞人”,而是指“小说”,也就是“讲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讲故事的人”和“变戏法的人”的确有点像。他们都借着某种技法来营造一种有别于平常现实的“奇观”。
受惠于西方现代小说的中国作家们都知道,小说的“戏法”有两种,一种是博尔赫斯式的,一种是马尔科斯式的,一个重在文本典故,一个重在地缘文化。而虹影的《上海魔术师》呢,却让人觉得有点十三不靠。这种不靠谱,往好了说,是赵毅衡所褒扬的“有法无天”,是苏童所赞叹的“奇诡莫测”;但是,往坏了说,却是一种不伦不类,一场语言的大冒险。
语言,准确说是“杂语”,是虹影在她这部所谓的“语言实验小说”里着力标榜的。中国自晚清白话文运动以来,从“胡适之体”、“鲁迅风”,一路到“毛文体”,现代汉语一直走的是一条以潜白为指归的单行道,与讲求瑰丽的古汉语背向而驰。可以说,整个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不断简化、纯化、单一化的过程。但是——想要在《上海魔术师》这样一个讲述旧上海杂耍班子故事的小说中,担负起为中国现代汉语开拓新的“星系”的巨大使命,虹影之吃力不讨好,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一无拉伯雷式的欧洲狂欢文化的传统,二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俄罗斯“心理现实主义”,既没有语言的僭越,也没有灵魂的拷问,虹影口口声声所谈的中国的“杂语”写作,其所谓的“自觉意图”,又如何体现呢?总不能为了杂语而杂语吧。《上海魔术师》中描写的四十年代的大上海,那个时候的确五方杂处,土洋杂陈,说十里洋场是个杂语的场所,也不为过。但是在小说中,这种杂语被极度夸张了、变形了,张牙舞爪,还口吐莲花。这已经不能说是小说的语言了,而是彻头彻尾成了诗的语言。这种充满诗性的失控,在那个所谓的“兰语”——女主角兰胡儿说的语言那里,达到了高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HIGH到了极点,尤其是一到男女两情相悦的时候。
《上海魔术师》,的确让人左右为难。是把它当一部现实的小说呢,还是当成一部作者用以自况的写意小说呢?这种为难背后,是作为诗人的虹影和作为小说家的虹影之间的矛盾。在《饥饿的女儿》这样的自传体中,虹影还能将语言、故事、情感三位一体,但是一旦落笔到旁人,她那作为诗人的天性,就往往按奈不住要跳将出来抒情。语言和现实的皮肉分离,也就在所难免了。《上海魔术师》是虹影“重写海上花”系列的最后一部,这也许是件幸事,因为老实说,上海对她而言,既算不上精神的属地,也更不是语言的故乡。她最终的归属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女人,这才是她小说“戏法”的真正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