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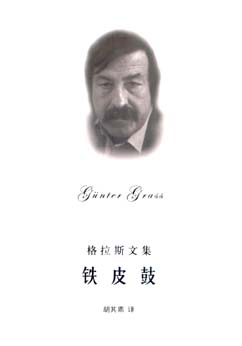 格拉斯是阿瑟·叔本华的老乡,他们是但泽出身的两位最大的人物了。在我印象中,格拉斯没有明确表述过他对那位同乡先贤的态度,他不是思想型或学者型作家,似乎不太热衷于哲学,哪怕是文学色彩很浓的叔本华哲学;但我敢肯定,他受了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巨擘的根本影响,我之所以说那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如果说格拉斯有格拉斯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的根本也是悲观主义。 格拉斯是阿瑟·叔本华的老乡,他们是但泽出身的两位最大的人物了。在我印象中,格拉斯没有明确表述过他对那位同乡先贤的态度,他不是思想型或学者型作家,似乎不太热衷于哲学,哪怕是文学色彩很浓的叔本华哲学;但我敢肯定,他受了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巨擘的根本影响,我之所以说那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如果说格拉斯有格拉斯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的根本也是悲观主义。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刚生出来,就有了宿命论的念头,就想到了死:“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可以说,奥斯卡一落地,就是个悲观主义者;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他的悲观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得到了加剧,小说最后,奥斯卡阴差阳错地被捕,被强行送入疗养与护理院;在医院那似乎是白色的世界里,他唱的是一首献给“黑厨娘”的歌谣,在歌中反复出现的是“真黑”这两个字。
也许格拉斯看到的,并不全是黑暗;但他对人类社会不断重现的罪恶是警惕的。他于2002年出版的新作《蟹行》讲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即1945年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被苏军潜艇击沉,船上近万人丧命,其中有4000多少儿。在他眼里,自始至终,直到现在,围绕这起灾难的,全是罪恶。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号称在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曾大肆辱骂格拉斯这样的异议分子为“犭更”,这是一种小型犬,没病时也像得了狂犬病,为着某个目的,连荆棘都敢上。艾哈德之所以如此仇恨并藐视格拉斯那样的作家,是因为他几乎每出台一项政策,都会招致他们的批评。而在他的前任阿登纳治下,知识分子似乎都比较乖,只要有奖金拿,就甘愿“莫谈国事”。艾哈德这么一骂不要紧,“犭更”们吠得更厉害、跳得更起劲了。至少格拉斯是如此,他与在野的社民党领导人格兰特成了好友。
其实,在艾哈德之前,格拉斯就不屑于政府的奖金,就爱议论政治。以他出生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他出生的地方(但泽位于德国和波兰交界处,这两个国家很少是睦邻,但泽历来是两国纷争最激烈的兵家重镇,所以是欧洲最伤感的城市之一,其历史整个是一部灾难史)、以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他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儿子)、以他成长的背景(参过军、当过俘虏,还当过难民、打过工,早年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格拉斯必然要从政治的角度来从事文学,而且必然是左派,但他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幼稚的左派。
1968年,具有明显左派倾向的大学生运动高涨;他既反对政府出台的以压制运动为目的的《紧急状态法》,也指责大学生们的乌托邦冲动和非理智举动;为此,他不仅没有成为青年的导师,竟然成了青年的敌人。
除了早年具有玄秘色彩的诗,格拉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政治(或泛政治)色彩,而且他紧盯德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热点,以至有人嘲讽他“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如《铁皮鼓》说的是二战;长篇童话小说《鲽鱼》谈的是性别政治,尤其是妇女问题;科幻小说《红母老鼠》讲的是地球面临的原子弹威胁;而《蟹行》讲述的与其说是个军事事件,还不如说是个政治事件,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态度的探讨,则完全是在政治格局中展开的。
他的晚期小说,以《蟹行》为例,完全剔除了早年的繁复、虚化和夸饰风格,显得遒劲、朴实、直接,踵事增华、左右开弓变成了提纲挈领、集中打击,哪怕是惊心动魄的环节,他也没有重彩浓墨,一般的考证和交代,他都是一笔带过。有人会说,格拉斯老了,文笔中的血肉少了,色彩淡了,已没有早年生龙活虎的劲儿了。但我却更喜欢他这种似乎干巴巴的精道风格;在我看来,他早年那种肥嘟嘟的文风固然显示了包举的才华和强劲的力量,但也是才华和力量的浪费,所谓矜才使气也。他晚年的风格更亲切,像聊天,也像聊天中的辩论。或许,格拉斯觉得,他早年意识到的种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他已年逾七十,已没有时间浪费在曲折而浩荡的笔法上了,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观点摆出来,让能领悟的人们早点领悟,让能预防的事情早点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