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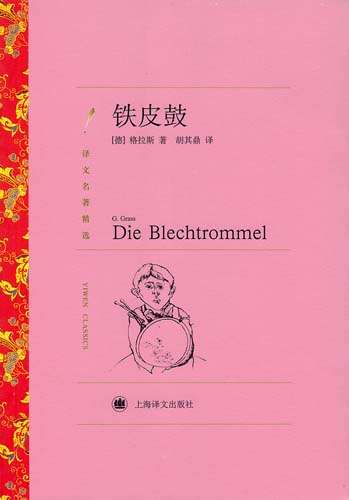 说起君特·格拉斯,稍有西方当代文学常识的人立刻会想到他的《铁皮鼓》,想到格拉斯那荒诞而诡谲的小说艺术。格拉斯用一个侏儒的流浪一生,编织成一幅以纳粹主政德国时期为背景的“百丑图”,格拉斯层出不穷的“魔术”与“花招”已经令中国读者目眩神迷,哪里还顾得上追踪格拉斯小说艺术的背景信息:关于格拉斯生平与政治见解的密码。 说起君特·格拉斯,稍有西方当代文学常识的人立刻会想到他的《铁皮鼓》,想到格拉斯那荒诞而诡谲的小说艺术。格拉斯用一个侏儒的流浪一生,编织成一幅以纳粹主政德国时期为背景的“百丑图”,格拉斯层出不穷的“魔术”与“花招”已经令中国读者目眩神迷,哪里还顾得上追踪格拉斯小说艺术的背景信息:关于格拉斯生平与政治见解的密码。
而据说,这些线索就隐藏在格拉斯的“政论小说”与“自传性作品”之中。在格拉斯逝世的噩耗传来之际,我们特意采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与译林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见识格拉斯文学成就的另一面:一个不只是在一旁隆隆“敲鼓”的介入者。
格拉斯“政论小说”
与中国读者的隔膜
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裴胜利同时也是格拉斯文集中译本的责任编辑。谈起上海译文出版社引介格拉斯的缘起,还需追思已故著名翻译家胡其鼎先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其鼎先生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他最早译了《铁皮鼓》的一个章节,刊登于《外国文艺》,没想到引起读者与作家的热烈响应。于是,裴胜利等上海译文社的编辑鼓励胡先生译完此书。
回想当年的出版江湖,裴胜利不免感慨连连。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间的业务交流非常频繁,两个出版社相互赠书,编辑们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两社甚至共同协商一个选题,不像今天这样彼此竞争。改革开放打破了外国文学出版的停滞局面,国内出版界开始大量译介德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德国古典四大巨头”的作品。“我们甚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达成默契:我们出歌德,他们出海涅,我们出席勒,他们出莱辛。”裴胜利说。
而直到1990年,《铁皮鼓》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裴胜利记得,此书一经推出,上海作家协会马上购入几百本,作家会员人手一本,作为学习范本。因为人们觉得格拉斯的写作手法很新颖,国内为此还兴起一阵模仿格拉斯式黑色幽默的热潮。1999年,格拉斯获得诺奖,上海译文社捷足先登,又买下格拉斯《我的世纪》的版权。这本书由中德版权代理人蔡鸿君先生翻译,居住在德国的蔡先生与格拉斯本人过从甚密,可谓近水楼台。
谈及《我的世纪》一书,裴胜利认为它的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个故事,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清朝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一直写到1999年作者的母亲103岁的自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是不折不扣的鸿篇巨制。此后,上海译文社又陆续将格拉斯其它八本书收入袋中,并在2005年推出十卷本《格拉斯文集》。
据裴胜利介绍,除了格拉斯几部广为人知的作品,十卷本《格拉斯文集》中的其它几部作品同样值得关注。譬如,《铃蟾的叫声》和《蟹行》的写作手法较传统,很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其他几部作品如《辽阔的原野》,是典型的政论小说,揭露两德时期深层的社会问题,与中国读者隔膜较大,不太好理解。在书中,格拉斯直言两德合并是失败的,经济和思想没有实现很好的接轨,实为操之过急之举。
格拉斯自传性作品中的“最终命题”
相比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引入格拉斯作品方面有首创之功,译林出版社稍稍迟了一些,却真正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亦如译林出版社编辑陆志宙所言,由于在译林社关注格拉斯作品之前,兄弟社上海译文社已经推出格拉斯的几部重要代表作。“我们还是很希望引介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又要有所区别。恰好格拉斯的《剥洋葱》与他的虚构类作品有所差异,是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作品。于是,我们从《剥洋葱》入手,陆续引入格拉斯的几部作品。包括《剥洋葱》、《蜗牛日记》、《盒式相机》以及《诗歌的战利品》。”
根据陆志宙的理解,在格拉斯的文学王国中,他的自传性作品无疑有着特殊的地位,阐述了作者对“回忆”与“记忆”的独特理解——他始终在提醒读者,回忆是主观的,回忆是不确定的。
在过去,中国读者更多关注格拉斯的虚构类作品,而从《剥洋葱》开始,格拉斯的隐秘经历与复杂人格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陆志宙看来,与英语文学相比,德语文学还是一个偏小众的领域,中国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背景比较陌生。其实,格拉斯的自传性作品,更充分地表达出格拉斯的艺术观,探讨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最终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