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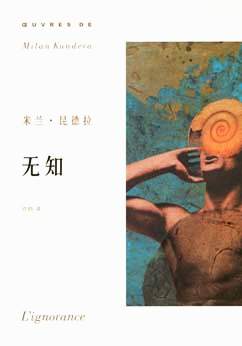 昆德拉的《六十七个词》中有“家园”一条,解释为:“有我的根的地方,我所属的地方。”接下来所说语气之果决,在其笔下素所鲜见:“家园的大小仅仅通过心灵的选择来决定:可以是一间房间、一处风景、一个国家、整个宇宙。”多年以后他写《无知》,看法似乎有所动摇。不过“词典”中另有一条“缺乏经验”:“我把缺乏经验看作是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人生下来就这么一次,人永远无法带着前世生活的经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人走出儿童时代时,不知青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结婚时不知结了婚是什么样子,甚至步入老年时,也还不知道往哪里走: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大地是缺乏经验的世界。”与有关“家园”的说法结合起来,也不妨认为作家自此开始一番思考:“家园”以及对“家园”可能的回归,是否也在“缺乏经验”之列呢。——对当时的昆德拉来说,尚且不存在这种可能;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虚悬一个“家园”的情境。《无知》可以看作思考多年的结果。 昆德拉的《六十七个词》中有“家园”一条,解释为:“有我的根的地方,我所属的地方。”接下来所说语气之果决,在其笔下素所鲜见:“家园的大小仅仅通过心灵的选择来决定:可以是一间房间、一处风景、一个国家、整个宇宙。”多年以后他写《无知》,看法似乎有所动摇。不过“词典”中另有一条“缺乏经验”:“我把缺乏经验看作是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人生下来就这么一次,人永远无法带着前世生活的经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人走出儿童时代时,不知青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结婚时不知结了婚是什么样子,甚至步入老年时,也还不知道往哪里走: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大地是缺乏经验的世界。”与有关“家园”的说法结合起来,也不妨认为作家自此开始一番思考:“家园”以及对“家园”可能的回归,是否也在“缺乏经验”之列呢。——对当时的昆德拉来说,尚且不存在这种可能;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虚悬一个“家园”的情境。《无知》可以看作思考多年的结果。
如果前述有关“家园”的说法意味着某种指向的话,《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萨比娜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六十七个词》中另有“背叛”一词,乃是专门形容她的:“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但是这一“美妙”感觉,萨比娜并不能够受用终生。小说写道:“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于是,“萨比娜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在那个与“家园”相反的方向上,她已经走到了尽头。
当萨比娜陶醉于“背叛”时,她是背对着家园的;《无知》里的伊莱娜和约瑟夫——两位同样流亡海外多年的“波希米亚人”——好比萨比娜转过身来。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却安排萨比娜始终义无反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这使我们联想起,《无知》写到一位捷克诗人,曾经预言笼罩自己的悲苦将持续三百年之久;“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对此,作家说:“如果说预言错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当时而言。”同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关于萨比娜命运的预言可能也错了。——假如她未及辞世,那么也将与伊莱娜和约瑟夫面临同样问题:《六十七个词》中所虚悬的那个“家园”,已经实实在在展现在眼前,等待着你的回归了。
《无知》正是由打这儿写起。伊莱娜和约瑟夫仿佛是仍然活着的萨比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形容萨比娜说:“她对故土的兴趣越来越淡漠了。”——这显然代表了昆德拉自己当时的立场;就像前述关于“家园”的描述,反映了他那不可断绝的向往一样。伊莱娜和约瑟夫不过是从萨比娜的立场稍稍松动,他们的回国之举都很勉强——约瑟夫是要满足已故妻子的遗愿,他甚至被认为患有“怀旧欠缺症”;伊莱娜则受到朋友一再鼓动,而朋友的话分量很重:“你这可是大回归啊。”
“大回归”——这是可以与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重返故乡相比拟的伟大举动。关于后者,作家有着深刻理解:“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真正的dolce 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然而,“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流亡生活与此毫无可比之处。”——约瑟夫也如此。对于现代的流亡者来说,“回归”反而是走向“未知”;其间毫无“激情探索”,因此也就无从“赞颂”。尤利西斯的“有限”,成了他们的“无限”。——昆德拉曾说,萨比娜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现在伊莱娜和约瑟夫所承受的,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果说《奥德赛》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分别揭示了这世界的两个极向的话,伊莱娜和约瑟夫则在其间无所适从,乃至走投无路。他们企图追随尤利西斯,抵达的却是萨比娜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