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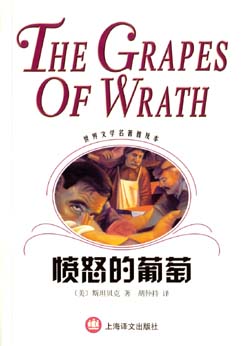 近日在工作之余,我重读了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该作品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向西部加利福尼亚迁徙的故事。读后,引起了一些联想。 近日在工作之余,我重读了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该作品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向西部加利福尼亚迁徙的故事。读后,引起了一些联想。
为了改变生存的环境,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说迁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实行的时候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人类同时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在这当中,有些障碍是先天的,诸如人的素质、智力、体力等,有些则是后天的,如等级、户籍等等。要逾越这些障碍,就必须付出代价。以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可称为“迁徙小说”的《姊妹花》(作者文夕)中的主人公、双胞胎滕林和滕枫为例,该姐妹俩因不满内地小城镇的闭塞和守旧贫穷的生活,先后迁徙到沿海开放城市深圳。
经过艰苦的闯荡和奋斗,她们在深圳都双双跨越了种种障碍,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她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姐姐滕林为过上有车、有别墅的衣食无忧的生活,竟然放弃了与自己相恋多年的男友,甘当老板钟兆威的情人;妹妹滕枫为了开办自己的公司,却遭到男友肖安的背叛,且男友为了惩罚她而自己付出了生命。这就充分说明,对一个迁徙者来说,要在陌生而复杂的异地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诚然,有些代价是无所谓的。它们要么是因为社会不公,要么是因为闯世界者本身的素质。如上举的《姊妹花》中的肖安,此人的素质较低,他不能承受在大都市里取得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迅速的成功给他带来的不是更大的进取动力,而是堕落和腐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这种带着伤痕的迁徙,构建了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潮流,没有这些人口的流动、迁徙,就很难想象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也难以想象中国社会市场化会有如此巨大的进展。
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异地移民、搬迁,包括我们百色市实施的“下山进城入谷”移民战略,正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迁徙者的命运却还没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上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他们的故事仅仅停留在“淘金”、“冒险”上,他们的形象也还仅仅限于打工挣钱。他们丰富的人性、人格,他们进取的开拓者气质,他们矛盾、痛苦的精神裂变,他们对命运的挑战和忍受,在文学中都没有得到典型的表达和反映,他们的命运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而新生代小说主要描述当今大都市中小知识分子的“零余”生活,“感伤”、“颓废”、“无聊”等等一时间成为这类小说的主导情感。由当初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演变而来的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则主要关注各种边缘文化群体的生活境遇,唯独“迁徙文学”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当然,对我们百色市而言,近年随着移民工程和“下山进城入谷”战略的实施,不少文学工作者对迁徙农民群体已引起极大的关注,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迁徙者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像岑隆业的长篇报告文学《百色大地宣言》、《同饮一江水》就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时代的要求相距尚远。为了全面反映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的画廊,我热切呼唤新的“迁徙文学”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