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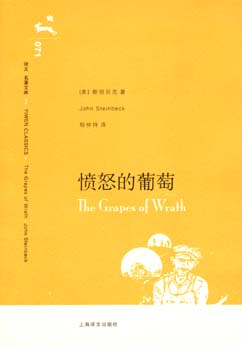 好莱坞电影机制的敏感早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知名作家打个喷嚏,就有制片人拿起计算器噼里啪啦地做改编预算。所以像《愤怒的葡萄》那样曾经在排行榜首逗留一年之久,作者斯坦贝克又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如果按照我国文学批评的一般口径,《愤怒的葡萄》的主题很容易就给钉死在阶级斗争的光荣柱上,但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老板不这么想——至少不全这么想。除了小说的影响力已经替票房保底之外,他们更看重小说本身的技术特点:一本几乎完全靠对话和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小说,实在是天生适合视觉化的。对付这样的小说,编剧纳内利·约翰逊和导演约翰·福特只需要将其中本来与故事主线一唱一和的时代背景材料(它们原本单独汇聚成所谓“插入章节”,interchapters)“先擀扁再搓圆”,充实到分镜头剧本的各个环节,然后让摄影师调度各种手段渲染亨利·方达的阳刚魅力,一个左翼电影的经典毛坯也就基本塑成了。 好莱坞电影机制的敏感早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知名作家打个喷嚏,就有制片人拿起计算器噼里啪啦地做改编预算。所以像《愤怒的葡萄》那样曾经在排行榜首逗留一年之久,作者斯坦贝克又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如果按照我国文学批评的一般口径,《愤怒的葡萄》的主题很容易就给钉死在阶级斗争的光荣柱上,但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老板不这么想——至少不全这么想。除了小说的影响力已经替票房保底之外,他们更看重小说本身的技术特点:一本几乎完全靠对话和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小说,实在是天生适合视觉化的。对付这样的小说,编剧纳内利·约翰逊和导演约翰·福特只需要将其中本来与故事主线一唱一和的时代背景材料(它们原本单独汇聚成所谓“插入章节”,interchapters)“先擀扁再搓圆”,充实到分镜头剧本的各个环节,然后让摄影师调度各种手段渲染亨利·方达的阳刚魅力,一个左翼电影的经典毛坯也就基本塑成了。
且慢,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愤怒的葡萄》的改编之路并不顺畅,明里有来自右翼的政治阻力——当时禁止小说发行的州政府就跟在议会中谩骂斯坦贝克的议员一样多,俄克拉荷马州甚至阻挠电影公司到那里去取景;暗里,那些给电影公司“输血”的财团老板也没少施加压力——要知道,这本书攻击的对象,正是这些将农民逼得无路可走的资本家。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成品,难免带上巧妙的、妥协后的痕迹。弱化对话里的火药味也好,减轻人物命运的悲惨程度也好,都被编导处理得遮遮掩掩、小心翼翼,散见于各个段落而不容一一细表。最明显的例子是,电影的高潮部分聚焦在乔德一家进入联邦政府的收容所,此时人物境况有所改善,银幕下,刚刚还一掬同情之泪的观众也暗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知道的是,小说原来安排人物离开收容所后遭受的重重打击,已经被编导悄悄地挪到了高潮之前。人还是这些人,事还是这些事,但结构轻轻一动,整个故事的基调就呈现两种曲线,小说徐徐低回,而电影渐渐昂扬——变化不多不少,正够用来卡到那条让各路大佬欣然点头的审查基准线。
说到“审查基准线”,那还真是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全凭英雄欺人的金线。图像比文字有更大的冲击力和普及性,所以不管是古今中外,“金线”总是更多更严厉地卡在电影而不是小说创作者的脖子上——起初是别人不由分说地套上来,勒得多了,编导们自己就学会调节脖子的长短粗细柔韧度,力求让伤口最小,没准有时候还近乎舒适。所以时至今日,“过审学”早已分出诸多流派,事先拍好N种结局请审查官挑选的招数,也成了制片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回过头来看,平心而论,在这类由于非技术因素(最多见是意识形态)造成“技术处理”的案例中,七十多年前的《愤怒的葡萄》应该还算四角俱全的,至少没把小说的面孔改到五官挪位,生生地变成一宗车祸现场。
比“车祸”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大概是“腰斩”。前两年,被电视里的“纯爷们”李云龙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兴冲冲地去找《亮剑》的小说原著,才发现原来并不只是言情电视剧会拒绝透露“王子与公主是否真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历史题材的也同样如此。李云龙能立下赫赫战功,却拗不过时代悲剧,小说后半段如一阵飓风般将英雄卷携而去的反右与“文革”在电视剧里是一片空白,李云龙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的子弹——用楚云飞送他的勃朗宁——也只在小说里才闪着幽冷的光。《亮剑》当然不是什么碰不得的名著,但这样手起刀落、腰斩两段的改法,还是让人在体谅编导难处的同时,油然而生某种荒诞感。
比《亮剑》更倒霉的是电影《活着》。张艺谋知道,余华原著里的结尾——只剩下一个老人和一头牛——调子太灰太绝望,于是在画面里加上一个孩子(前提当然是改变原著的情节,让福贵家好歹保全下一支血脉),同时安排一段著名的、希望与反讽并存的对话:“鸡长大会变成鹅,鹅长大会变成羊,羊长大会变成牛,到那时,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尽管如此苦心孤诣在当时并没能换来一张公映通行证,但电影《活着》对结尾的处理,至少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光明的尾巴”的理想模式。相比之下,前不久《神探亨特张》将近结尾时,中年妇女推开窗户慷慨吟诵的那段励志台词,就要突兀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