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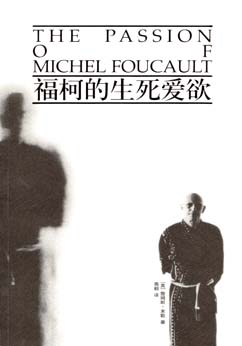 ■在本书中,主人公正是饱有这样一种哲学气质:他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历史界限,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超越这种界限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好奇心的自我认知史。 ■在本书中,主人公正是饱有这样一种哲学气质:他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历史界限,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超越这种界限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好奇心的自我认知史。
■福柯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没有陷入世俗理性和道德的逻辑陷阱中,而是在狄奥尼索斯式光耀中展开对自身不倦的审美探求。
■哲学生活,在福柯这里,不是一种有主次之分的修饰性短语,不仅仅意味着生活在激发哲学,而是意味着,哲学和生活在相互生产和交织。
在晚年,福柯在其影响甚大的《什么是启蒙》的结尾,提出了我们自身的本体论的批判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对康德这样一个问题的呼应:我是谁?但是,不同于康德的是,福柯并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有待发现的我的本质。相反,“我”只是一个可以被反复发明的东西,它并不被一个呆滞的先验秘密所主宰,“我”处在一个未知的变化和生成的过程之中。对这个“我”的本体论批判,就不是一劳永逸地获得他的秘密,而是创造一个不可知的自我,将自我纳入到一个无尽的生产和发明过程中,将自我当做一个艺术品去反复地锻造,因此,这样一种对待自我——创造自我、发明自我——的意志,被福柯看做一种气质,一种态度,一种哲学生活。这样一种哲学生活,就是要不断地探讨自我的界限,同时也要探讨跨越自我界限的可能性,前者能够表明界定自我的权力存在于何处,后者能够表明自我在多大程度能够跨越各种权力从而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因此,自我的本体论批判,既是对自我的“界限进行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种界限的可能性的一种检验”。
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主人公正是饱有这样一种哲学气质:他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历史界限,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超越这种界限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好奇心的自我认知史。这种认知不是一种悲怆的承受苦难的心灵史,也不是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光荣的传奇般的成名史,这是将自身作为一个试验品的美学史。因此,哲学家的生活历史既不是被一种悲凉的氛围、也不是被一种喜剧的调子所笼罩。这样一种历史注定不是情感所左右的心理剧,也不是一个道德主宰的悲喜剧。这个历史——福柯的自我认知史——既冲破了道德的禁锢,也要将人从心理学的深度中解放出来。人,在这里,并不被一种确定性的真理知识所定义,相反,人,纳入到审美的范畴,被当作一种艺术品来对待。福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人,而詹姆斯·米勒也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福柯——在这本书中,福柯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没有陷入世俗理性和道德的逻辑陷阱中,而是在狄奥尼索斯式光耀中展开对自身不倦的审美探求。其最终结果,其自我认知的意志,并不在某一个特定的完结时刻给自己下一个终极定义,而是将自我推到一个不可知的位置,推到某种可能性/不可能性的边缘,推到某一种危险的面临死亡的处境,以此来检验他的极限。这样,自我认知就必须通过无休止的自我实践来完成。
在米勒所勾画的福柯的这幅肖像里,哲学和自我实践有一种惊人的相互生产性,它们在彼此追逐:哲学知识似乎是对自我实践的辩护,同时,自我实践似乎也是哲学的满足形式和发展形式。福柯的哲学,首先是关注他自身的哲学,是探求自我秘密的哲学,其次才表现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形式;而福柯的实践,又为关于自身的哲学知识提供了证据,为这种理论形式找到了突破性的支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这里,正如德勒兹有一次对福柯所说的,“任何没有碰过壁的理论都是不可能发展的,而实践就是用来凿穿这堵墙壁的。”在此,自我实践,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自我技术,并没有一个世俗的针对性目标,而毋宁说是在不断地摆脱和凿穿世俗的目标,也是在不断凿穿既定的有关人的理论知识。如果说自我实践确实存在着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自我的限度何在?自我的哲学知识何在?自我的知识能够借助怎样的自我实践而展开?或者用米勒的话说就是,福柯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形式的强烈欲望,而他的生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将这欲望付诸现实的执著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