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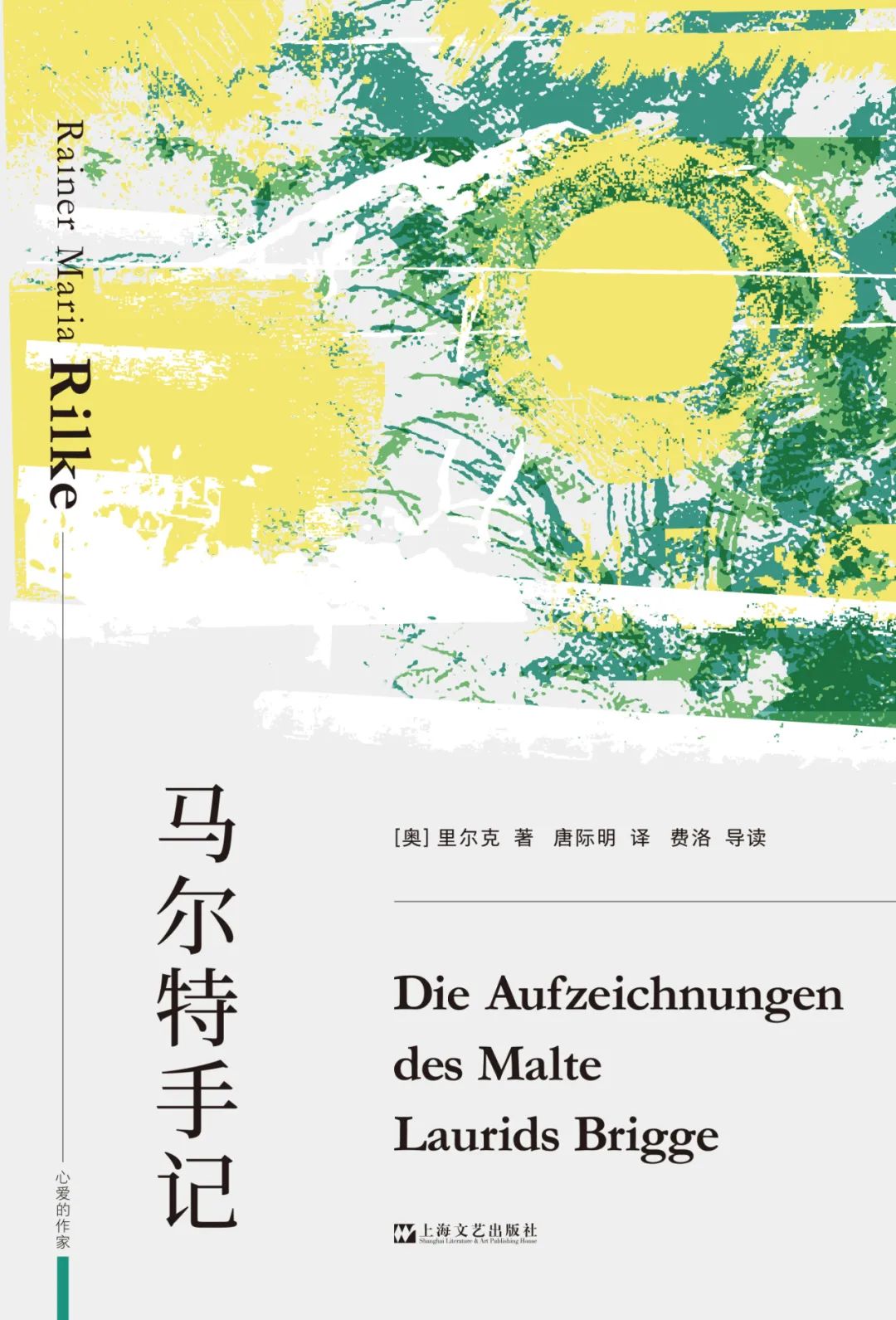
《马尔特手记》
[奥] 里尔克 著
唐际明 译
艺文志|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译本导读
“成长者”马尔特
文|费洛
伟大的德国小说,在堪与媲美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小说之外,孕育出两个独擅胜场的类别,一类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另一类是“艺术家小说”(Künstlerroman)。“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心智初开的青年,立志于探索人生和心灵的最高境界,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向这一境界的成长,当成长的力量来自诗和艺术,“成长小说”便会与“艺术家小说”融合。“艺术家小说”叙述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是诗歌、音乐或绘画精神的化身,凭靠此种精神成为英雄,完成他的伟业;艺术家小说探讨他的生活方式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爱情、婚姻、家庭、友情、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当艺术家的心灵成长凸显为主要问题,“艺术家小说”便与“成长小说”融合了。
里尔克的这部《马尔特手记》,正是融“成长小说”与“艺术家小说”为一体的“艺术家-成长小说”(Künstler-Bildungsroman),且以最为独特的方式将之推向了巅峰。有别于同类小说此前著名的先例,如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其主人公踏上一条“外在的”游历之路,去追寻某种理想中的事物(当然,游历于外部世界的追寻过程,象征着内心世界的成长过程),《手记》的主人公来到巴黎并居留于此,但巴黎并非他游历外部世界的终点,倒是他内心世界之成长的起点,是他踏上的那条“向内之路”(Weg nach Innen)的起点。
《手记》的主人公马尔特出生于北国丹麦,全名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某个秋日,他独自抵达巴黎,落脚于拉丁区图利耶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穷困潦倒地度过了那年的秋天和冬天,迎来了次年的春天。他何时离去,无从知晓,他的离去和到来一样不着痕迹。可是,逗留巴黎的这段时间内,他在四壁萧然的旅馆房间里写下一篇篇手记,记录了内心发生的深刻改变和脱胎换骨的成长。
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形单影只,身无长物,他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是与传统脱离联系的现代人。最初的抵达,立即在他身上触发了一系列的“巴黎印象”,这些印象围绕感官遭受的种种外界刺激——闻到的气味,听到的声音和见到的景象。巴黎日常生活里的各种气味和噪音,甚至片刻的寂静,都会令他不安;而目之所见,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医院更是带来恐惧。这些印象紧紧缠绕着他,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恐惧与不安,挥之不去,至多只有短暂的停歇。
……
如何对抗这无所不在的“恐惧与不安”?马尔特是一位诗人,求助于写作。可他此前写过的诗受着情感的摆布,都是不成熟的吟风弄月。事实上,他的诗尚未开始。他必须首先成为“初学者”,一位“成长者”。这意味着,不再执念于自己是迟到的“后来者”,要将人类的一切发明、进步、文化、宗教和世界历史置诸脑后,让自己从“先来者”的数不尽的遗物里挣脱,回到自己此在之初的本原,从而成为“最先者”。如此方能在成就自己的寂寞里成长,开始他的工作。这正是他在纲领性的第14篇手记里做出的决定:
这位年轻的、无足轻重的外国人,布里格,得在五层阶梯高之处坐定、书写,日以继夜。是的,他必须写,这将会是个了结。(见本书第23页)
为了回到此在之初的本原,他着手“童年回忆”的写作(15)。尽管这个主题很快被打断,他还要一次次地对抗自己的不安和恐惧(16-26),但最终,他得以在“五层楼上的”寂寞里聚精会神,专注对童年的回忆(27-44)。
回忆童年,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让自己重返假想中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美好年代,而是把生命之初的各种体验,以其本真的状态召唤到眼前。只有向着童年回忆,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些人生之初的铭心体验,才能将自己究竟是“谁”,从何而来,“我”的本质揭示出来。这些体验几乎与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全不相干,既包含爱、快乐、惊异和神奇之感,也包含焦虑、不安、畏惧和惊恐。对于像马尔特这样的现代人而言,后者的比重更胜于前者,更有必要予以特别关注。一旦他通过回忆把这些体验本真地召唤到眼前,他也就回到了自己此在的本原。他观看着身处这些体验的“童年之本我”,有如金蝉脱壳一般地从“一己小我”当中脱离出另一个更高的“我”,一个寓托“人”之存在的“大我”。这个“我”在“童年回忆”里不断地壮大,不断地提升。“一己小我”愈是向“童年之本我”敞开,愈是被后者充盈,这种脱壳和蜕变的过程就愈是彻底,好比是被之灵魂附体后,突然释放出一种久已尘封的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