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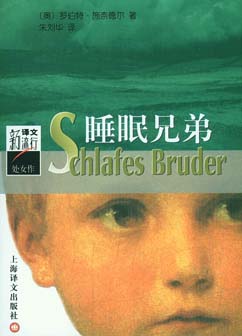 三 音乐家埃利亚斯的故事虽然被定位在了遥远的十九世纪,它却依然红透了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大陆,和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其实仔细一想,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作者罗伯特·施奈德尔毕竟也是后现代社会里的一分子,深谙现代人的种种情感体验和烦恼无奈:他笔下的埃利亚斯的怀才不遇,他的孤独落寞,他的爱情悲剧,既让当代读者暂时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冷漠与烦恼,也同时唤起了当代人对刻骨铭心爱情故事的渴望、对匆忙短促人生意义的追寻。 三 音乐家埃利亚斯的故事虽然被定位在了遥远的十九世纪,它却依然红透了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大陆,和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其实仔细一想,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作者罗伯特·施奈德尔毕竟也是后现代社会里的一分子,深谙现代人的种种情感体验和烦恼无奈:他笔下的埃利亚斯的怀才不遇,他的孤独落寞,他的爱情悲剧,既让当代读者暂时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冷漠与烦恼,也同时唤起了当代人对刻骨铭心爱情故事的渴望、对匆忙短促人生意义的追寻。
埃利亚斯拥有旷世奇才,虽然他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乐理知识和管风琴演奏技巧,但凭着天生的禀赋和领悟力,以其卓越超群的表演一度使人们瞠目结舌。作者多希望将埃利亚斯与苏格拉底、耶稣、列奥纳尔多、莫扎特等人齐名,但可惜他没有留下任何音符和节拍。他就如此被湮没在芸芸众生中,他的不朽创作也变成了飘散在空气中的影子,难怪作者要哀叹埃利亚斯是虽“降生了的,但究其一生又仿佛未曾来到这世上的”无名人物。
倘若真能默默无闻,埃利亚斯或许还能与世无争地在那穷山沟里四平八稳地生活下去,不至于在22岁时就结束自己的生命。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他因上帝赋予他的音乐天赋而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不仅没有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赏识,反而招惹了许多不必要的嫉妒、恼怒乃至怨恨:因为嫉妒管风琴师暗暗决定不再给他授课;因为恼怒父母将其锁在自家小屋里;恼怒日积月累久了,就成了怨恨,受着怨气支配的母亲还曾经秘密策划了一起谋杀,所幸的是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埃利亚斯身体变形后留下的烙印使他的超尘拔俗更加昭然于世,一时间,猜疑、谎言和诽谤不绝于耳,他既不能过一种正常人的普通生活,事实上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才能,在艾希贝格,他是一个形单影只的怪人、零余人。
看来,天才的成长道路总是要伴随着许多的磨难和坎坷,这和罗伯特·施奈德尔的个人成长、创作经历很有一些共通之处。在采访中,施奈德尔也表示书中确实有很多地方带有自传体色彩,埃利亚斯只是他无声的代言人。
小说中,埃利亚斯的代言人则是音乐。痛苦的情感经历和对爱情的执着乃至狂热构成了他音乐的主题和主旋律。一方面,他在音乐中持之以恒地坚持对死亡主题的探索:“基督的苦难”总是“激起他做曲的冲动”, “他爱一切可以跟死亡联系起来的东西”,在最后的演出中,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人如何同死亡做斗争”--那死亡,是“戛然的沉默,难以忍受的间歇”。另一方面,埃利亚斯在乐曲的旋律中追随着他的恋人--伊尔斯贝特的心跳声,因为他只是为她而演奏,为他的爱情而演奏。
在音乐中,埃利亚斯找到了表达他的伟大永恒爱情的语言,而在日常生活中,埃利亚斯则是个不善言谈的小伙子,虽然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悦耳动听。音乐成了弥补他拙嘴笨舌的工具,但是他的音乐并不为他的爱人所理解 :伊尔斯贝特虽然对他无比钦佩,但并不理解他的音乐是为她而做,也不理解他苦苦寻觅的心上人就是她。音乐和爱情终究不能相携着共同走完人生的旅程,而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这也就构成了埃利亚斯命运的悲剧。当埃利亚斯前生注定的、他所追求的没有任何肉欲的纯粹爱情希望被证明为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之后,他没有了生活的目标,不知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在现代多元化的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复杂、模糊起来,在众多的选择面前,年轻人常常犹豫彷徨,没了主见 ;埃利亚斯在这里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他需要为自己确定一个非此即彼的生活秩序和明确清晰的生活目标,于是,他选择了爱情。选择爱情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反对音乐,他的沉沦由此而注定--因为埃利亚斯毕竟还可以自主地支配音乐,而虚无缥缈的爱情则完全不是由他所能决定的,或者说不单单是由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埃利亚斯被自认为的伟大爱情折磨得疯疯癫癫,一蹶不振,在精神的极大错乱中,他将一名淫荡的表演派传教士的胡言乱语--“谁睡觉他就不在爱”--视为至理名言,并决定以身效仿--“在爱的人不睡觉”,仿佛以此就能证明自己爱情的不朽和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秩序。他向他的好朋友彼得解释道,人在睡眠时“不在爱。人们处于一种死的状态,因此死亡和睡眠被称作兄弟不是无缘无故的。睡眠的时间是浪费因而也是罪孽。一个人睡觉度过的时间,死后将会加在他在炼狱里的时间上。”在埃利亚斯的眼里,爱情已经不单单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她更是一种不能容忍任何短暂停顿的、无时无刻不在持续的行为;否则,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在爱。而埃利亚斯是不能接受这种虚情假意的存在的。为了自己的“一堆谎言和半心半意”他要惩罚自己,而他选定的惩罚方式就是剥夺自己的睡眠,过一种“清醒、崭新的生活。这清醒的崭新的生活将给他带来伊尔斯贝特的爱情和对天堂极乐的确信”。但事实上,埃利亚斯最后七天的生活完全靠曼陀罗等麻醉药草来维持,没有了清醒的理智,哪里可能有清醒的生活呢?或许是在天堂,或许等到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