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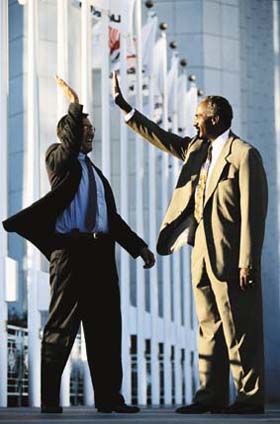 一些地方把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企业股本出售给企业经理持有,这为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线索。这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讨论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诸多障碍之中似乎有一个核心的两难抉择:允许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怕一下子“砸”了市场;不允许流通,那么中国的股市上永远只买卖企业的小股份,而不能提供交易企业控制权的机会。没有企业控制权的买卖,股市怎么可以厚实起来?但是,把一部分国有股出让给企业经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由于经理持有的股权是锁定的,即在经理任内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但持在经理手中的股本,只要数额不再是小得不足为道,就会大大强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潜能当然是扩展市场的基础。同时,随着经理人员的流动,经理所持的股权也逐步入市交易。因此,经理持股的不流动性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渡期,经理持股的效果会显著不同于绝对禁止流动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经理持股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现有的经理自己都没有多少钱,要他买够一个对其经理行为确实有制约效果的股本额度,钱从何来?基层的一些自发做法是通过某种集资或借贷关系,这里有没有让金融组织、特别是叫做“投资银行”的机构大展拳脚的机会,值得研究。总之,我的判断是,有了资本市场的配合。目前的“放小”政策有可能放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企业产权改革有了实质的、成规模的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有了最可靠的基础。 一些地方把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企业股本出售给企业经理持有,这为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线索。这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讨论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诸多障碍之中似乎有一个核心的两难抉择:允许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怕一下子“砸”了市场;不允许流通,那么中国的股市上永远只买卖企业的小股份,而不能提供交易企业控制权的机会。没有企业控制权的买卖,股市怎么可以厚实起来?但是,把一部分国有股出让给企业经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由于经理持有的股权是锁定的,即在经理任内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但持在经理手中的股本,只要数额不再是小得不足为道,就会大大强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潜能当然是扩展市场的基础。同时,随着经理人员的流动,经理所持的股权也逐步入市交易。因此,经理持股的不流动性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渡期,经理持股的效果会显著不同于绝对禁止流动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经理持股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现有的经理自己都没有多少钱,要他买够一个对其经理行为确实有制约效果的股本额度,钱从何来?基层的一些自发做法是通过某种集资或借贷关系,这里有没有让金融组织、特别是叫做“投资银行”的机构大展拳脚的机会,值得研究。总之,我的判断是,有了资本市场的配合。目前的“放小”政策有可能放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企业产权改革有了实质的、成规模的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有了最可靠的基础。
规范资本市场的动力机制
资本市场当然需要规范。不规范,“融资骗子”横行,投资人终究要被吓回去的。问题是“规范行动”的信息基础和激励机制。我刚才提到,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资源,一有机会它就要“冒”,活跃非常。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才能要大规模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条件。否则,自发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只能停留在一个临界水平以下,从社会经济的表层来看,就是所谓“企业家供给不足”,样样事情没有政府精英的推动和组织,好像就没有办法搞成。在一个长期以行政为中心的官本位的国家里,究竟能不能容忍企业家在经济舞台上人尽其才,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因此,说到资本市场的规范,首先是我们整个社会是不是能够容忍和鼓励企业家的创造,而不是扼杀或抑制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当然,资本市场上可能良莠不齐。这就是人们提到的代理问题以及经营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没有这些问题,由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也存在其他风险。市场规范其实主要是用来帮助当事人定约并恰当地分配风险的。在这一点上,正如汪丁丁所讲,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需要一整套社会支撑体系。比如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都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执行这些规范的制度保障。我们把这套直接搬来,当然也是一个快捷的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人家那一套是“上当”“上”出来的。最初的市场难免混乱,使一些投资者成为受害者,或者损害企业的利益。于是各方都要求规范已有的交易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经验会告诉当事人,有“猫腻”的市场总是“厚实”不起来的,那对买卖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规范市场的潜在利益会驱动规范进程。一旦规范市场的力量大到能够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时,资本市场就可以做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了。
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规范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那些“吃亏”的一方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来建立保护产权的制度。因此,为资本市场的立法要从“根”上头下手。这个“根”就是良好的财产权利的界定。界定清楚的权利产生可预期的收益,可预期的收益驱动人们保卫权利,权利和权利的平衡才能产生规则。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在初级的资本市场里以“公有制”名义包装的“糊涂产权”(比如赢了归代理人,输了归“公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得到良好界定的产权与之相比势单力薄。
作者简介:
周其仁,早年在东北完达山狩猎。1978-1982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前开始参加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后来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9-1995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几所大学访问求学,获UCLA博士学位。1996年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