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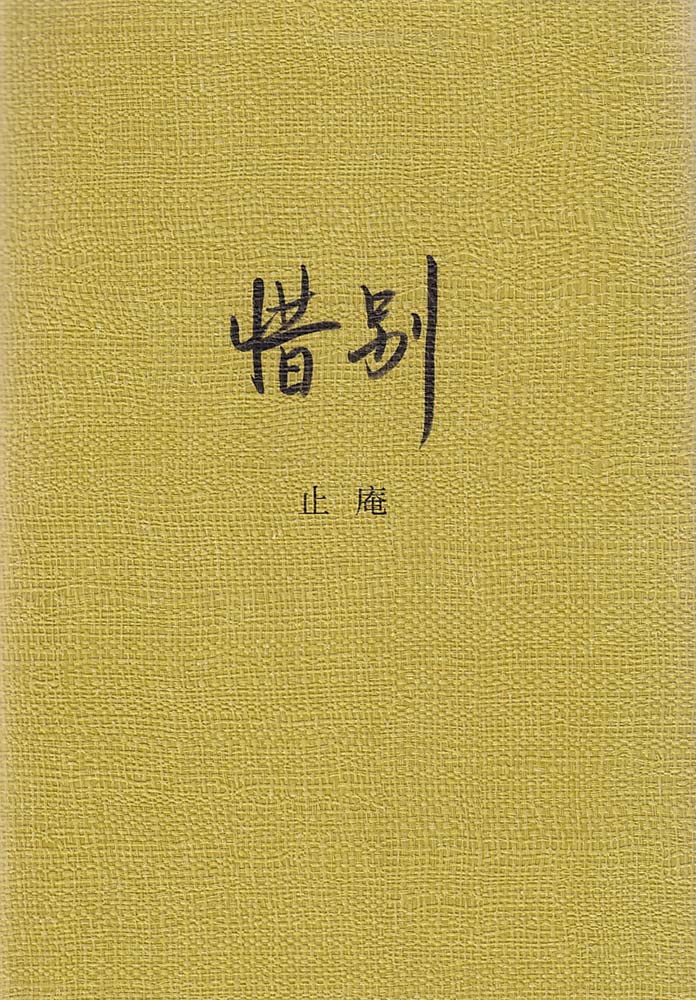 “止庵”这个名字,源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意思是说,人的心性不要学流水的起伏,而要学其静止澄澈,有分寸,有所不为。他向往周作人的内敛平和,即使是写母亲生死的《惜别》,也没有多数作家的惨痛,读来真挚绵长。 “止庵”这个名字,源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意思是说,人的心性不要学流水的起伏,而要学其静止澄澈,有分寸,有所不为。他向往周作人的内敛平和,即使是写母亲生死的《惜别》,也没有多数作家的惨痛,读来真挚绵长。
母亲故世后,止庵沉淀了三年,在母亲生前的房子里整理她的信件,照顾她的花草,感受她因邻居孩童吵闹带来的失眠——“仿佛重走了一遍她的这段岁月”。这些日子让止庵重新发现了母亲,老人是只争朝夕地热爱生活:她喜欢逛超市,喜欢吃肉粽子,爱看烟花,爱读推理小说,把洋娃娃当作子女陪伴,要拥有一间大玻璃窗的房子让阳光洒落下来……
众人都喜欢写传奇,止庵却独爱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不传奇的东西也有价值”。“母亲是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建树都没有,对普通生活的热爱就没人好好写过。”止庵决心为母亲写一本书,把这些真切结实的寻常时光记录下来。
《惜别》里,止庵细细讲述母亲的生活琐事,对于痛苦——身体或心灵上的,却轻轻带过。母亲最煎熬时也不过是说:“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不希望人家管束我,可我老了,又病了,那么重的病,让我太无奈了。”这种“节制”是止庵在写作上最看重的敬畏之心:既怕唐突了读者,又怕把自己美好的感情破坏了,“十分情感写到六七分即可,却常见众人六七分偏要写十分”。
周作人摘译过柳田国男《幼小者之声》里的这么一段文字:“假如真有不朽这么一回事,我愿将生活里最真率的东西做成不朽。与人的寿命共从世间消灭的东西之中,有像这黄昏的花似地美的感情。”止庵《惜别》里写的正是这样美好的感情,面对故去的人,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不要急急转身离去,而是尽可能多地相送。
对话
“普通生活没人好好写过,不写自己都慢慢忘记了”
大道:你之前研究周作人,研究张爱玲,他们对你的思想和写作都有什么影响?
止庵:这两个人是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里最好的,再加上鲁迅。张爱玲和鲁迅其实接近,都是比较尖刻透彻的人,我无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大道:但看你的文风十分温厚。
止庵:那就是因为周作人。周氏兄弟是两个极端,周作人在另一端。很多事情他也明白,但他不想说,鲁迅是不吐不快。在做文章的态度上我受周作人影响极深——漫谈式而不是讲演式。他尽量去体会人之常情,去描述普通的、正常的一面,并不是他不知道反面。
我可能骨子里比较像鲁迅,微博微信上也常流露出尖刻的一面,但气质上我更羡慕周作人,希望能努力变得平和。
大道:但我们不是常说要保留自己的棱角吗?
止庵:棱角在里面,不在有所为,而在有所不为。
大道:很多作家写母亲,会写惨痛的历史,下笔很重。《惜别》里你只轻描淡写勾勒出了母亲的轮廓: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遍游欧洲的富家小姐,积极投身过革命,也受过迫害……重点全在母亲最后二十年安稳生活的朝朝夕夕。这是刻意的吗?
止庵:这完全出于我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想回避什么。有些东西姑且不论它们有没有意义,至少我还没想明白写它们的意义。
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本备忘录,写我想记住的东西,我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不是她经受了多少苦难,而是最后日子里她对生活的珍视和热爱。这牵扯到我对上一代人生命价值的分辨,我不写没人写,我不写我自己都慢慢忘记了。
大道:这本书是致敬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
止庵:对,文学家都喜欢写传奇,我却独爱《一颗纯朴的心》。母亲是很普通的人,一辈子什么建树都没有,用某些标准来衡量是“一事无成”,但不是传奇的东西也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