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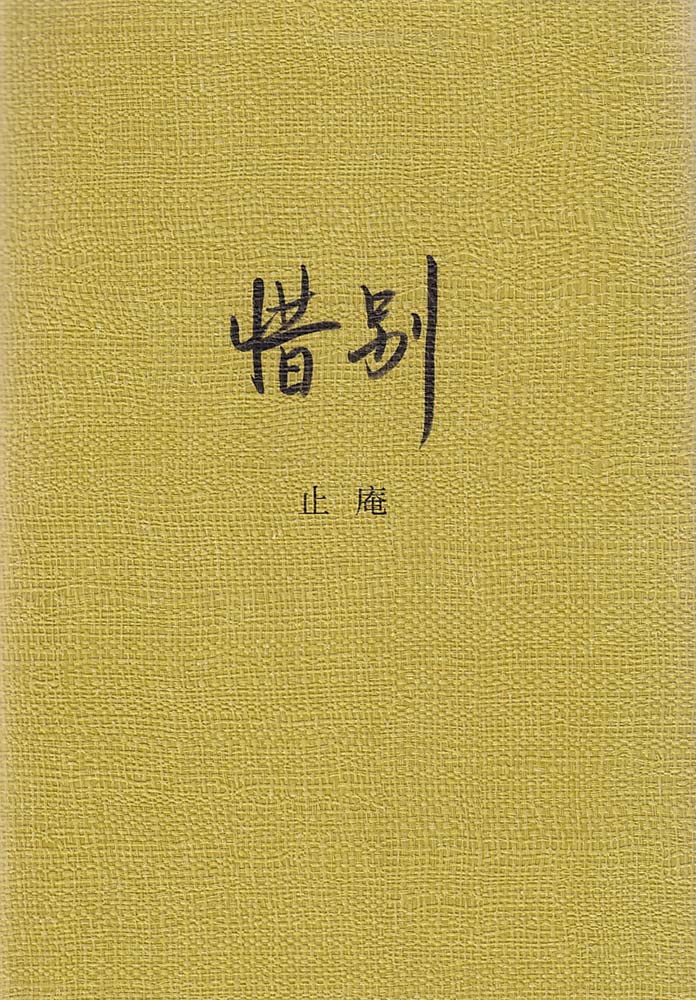 如果《惜别》的作者不是止庵,我大概不会有翻开它的兴趣。一般说来,我不太喜欢读悼念亲人的文字,觉得那样的情绪太私人化。再说,前人那么多珠玉在前,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或是归有光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又或是纳兰容若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似乎所有亲人逝去的惆怅、思念、悔恨、淡然都已经被说尽,今人再如何表达也只是苍白的重复罢了。 如果《惜别》的作者不是止庵,我大概不会有翻开它的兴趣。一般说来,我不太喜欢读悼念亲人的文字,觉得那样的情绪太私人化。再说,前人那么多珠玉在前,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或是归有光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又或是纳兰容若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似乎所有亲人逝去的惆怅、思念、悔恨、淡然都已经被说尽,今人再如何表达也只是苍白的重复罢了。
然而止庵写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悼文,他记叙的是自己在母亲离世后的岁月中,体会已经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想法和心境,一点点感受自己在慢慢离开“母亲”的世界的过程。贯穿在对母亲生前死后的日常生活记忆中的,是博学的止庵对古今中外“悼亡”思想强烈的个体共鸣和思辨,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文学的,那些原本只是存在于书本上的文字,在母亲死后,才对他个人有了真切的情感意义。止庵在母亲去世之后去日本,遇到称心的小物,马上想到永远没法再买了送她,看见各处好的景致,也想到永远不能告诉她了。
永远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但母亲去世了才使得止庵体会到,永远不过是有始无终的无底深渊,“永远如何”只是一种愿望,而“永远不能”才是真的—唯有死亡可称永远。
死亡对止庵沉疴已久的母亲来说,也许不是死者的不幸,但对生者而言,却是真正的不幸。止庵的母亲和大多数人的母亲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留下足以流传万世的锦绣文章,她所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品位,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然而母亲的离世,对所有的子女而言象征着母亲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母亲的肉身一并不复存在。止庵慨叹,“生死之间,与其说是界线,不如说是隔绝。无论‘给予’,还是‘接受’,都不再可能。无论已经去世的母亲,还是仍然活着的我,两方面的机会都被死亡剥夺了。”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死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一次是消失在所有人记忆中的死亡。止庵之所以将他这些极其私人化的悼亡文字公开,也许是有那么一点天可怜见的私心吧,希望自己的创造物多少可以延缓母亲那命定的、第二次死亡的来临。
|